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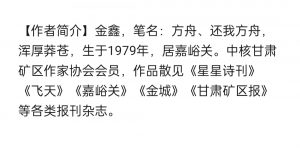
南宋 · 陈亮篇
一 、英雄初生
“危楼还望”,陈亮曾写道:“离乱从头说”。
——或如破烂的命运之书在硝烟中,
被马蹄戏踢,翻开的扉页随家族史诗,
泛黄于马尿下,被一阵风卷去。
时间产卵。而后秩序将铁,埋入坚硬的
事实:演绎时代磁性魔力,只对马背上
彪悍的祖宗,手里金戈的弧形存在敬畏。
岁月,用五世死生交叠之悍勇敲碎
祠堂的门楣,告诫荣耀之光的短暂。
阳光缓缓踱过黄昏,使日头渐凉,
父母蜷缩于生活,眼看着人形廊宇外,
一棵大树的枝叶凋零,余荫即将
旋转过堂榭的南墙,走向黯淡和落寞。
斗尖亭榭,还在祖父的眼底偶尔闪过,
但壮观的族群,动辄百人汇聚的背景,
勾勒出一幅烟雨蒙蒙的,江湖远景图,
反使得回忆,处处充满无奈和咸涩。
时间在蜡烛照亮的黝黑小屋里,闪烁。
壮丽的出生,跟随着烛光为黎明开幕,
祖父将铿锵的预言高高举过头顶,随着
婴儿一声洪亮的啼哭、飞溅于星星间。
受命于铁树一样挺拔和锈迹斑驳的族群,
既被脚下那块灰白色的盐碱地灼伤,
他也将,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和使命。
二 、锋芒毕露
祖先的期许透过纸糊的窗户,青鸾般落在
白玉案头,落在少年肩头,
烛火在槛墙上摇晃出捧经读卷时的倒影;
但堆积的兵书,仍使求知的胸腹饥渴难耐,
烦闷时,他走出家门,与星星独语。
十八岁的意气放逐在十九个缀着历史名人的书页的沙盘上,
陋室深居:双手拢袖筒,闭目沉思。
在心中厉兵秣马,推演《酌古论》,
当胸膛里兵马嘶鸣,残戈断戟散落一地之时,
有龙蛇游于穹苍,随笔尖激荡起惊世锋芒。
“他日国士也”,周葵叹曰:“请为上客”。
于此别离父母,收拾行囊,远赴婺州,
在尽显奢华豪富的庭堂,在折叠着十三学士图的屏风
和,杯觥交错之间谈兵论刀、醉酒时振臂高呼,
醒时又伏案、下笔如风,书写奏章;
闲暇时外出走动,一袭白衣胜雪,
使城池里豪俊青年纷纷跟随,化做繁华街景。
幕宾不过谋生,他更象一道耀眼的闪电,
划破云雾,使雷霆爆裂,
使周葵拂须含笑,胸膛挺起,红光满面。
在被赏识的六月,主家递来书籍的慰藉和赐赠,
翻开的《中庸》和《大学》里,
扉页坚守着道德心胜;他却去心的边缘,
去寻找榜样的灯塔,当救国的沙场渐渐灰白时,
忽然,明亮的灯光照耀胸膛:英雄气概诸葛亮。
此刻应当改名为“亮”:他想到。像一块石头
一样站着,除了梦想、镀了铜一般的倔强,
只有思想的光芒在一颗救国的心中闪烁游走,
走出庭院,一切都静止不动;
直到,精神一振,
奋笔疾书《英豪录》和《中兴遗传》,
直到,阵风吹乱了远处的朝堂,吹乱了胸膛里的热血。
三、报国无门
这一年的天空充满,烟与历史媾和后的甜骚味,
南宋与金朝的苟且,
就像罗曼陀花与醉鱼草混合捣碎后
投入湖水,使活鱼麻醉。
当世人多以“天下欣然,幸得苏息”窃喜时。
临安府外一只飞旋着的雏鹰正带着,
远啼之见和嘶哑之伤,被阻挡
在高高的南墙外,
被一簇簇焦灼狠狠撞击胸腔。
此时,血气方刚的年轻布衣,笔下正有万夫之勇,
冒着杀头之险,连上五书呈递朝堂,试图力挽狂澜;
石沉大海、渺渺无期的是,青年的慷慨激越,
连同《中兴五论》,带着超时代的狂悖,
从风的嘴里,吐出一堆饱含沙土的苦涩。
此时,秋风翻开的书页里不时泛溢出无边
落木萧萧下的遗憾和不甘,
陈亮心灰意冷,卷起行囊,掉头返乡!
宽广的乡土,将英雄从他寒冷的剑尖处归鞘,
让英雄砥砺内心,归于宁静,
温养他刚硬的脊梁,将他的荣耀暂存于此。
柳下授学、闲时锄耘,或雪地里习武练剑,
当白水渲染器皿的边缘,墨水下的两次
科举,终是文以载道,时难求同。
——“道不在于我,则虽仕何为”?
文人的情怀就像风的发梢,飘着
一层璎珞似的空明和冲动,
总被思绪拽着飘向疆土、祖国。
潜心治学、仁泽乡野,再次上书已是十年之后。
四、狂怪陈亮
这应该是端坐在临安府的南宋孝宗皇帝,
第一次翻阅和读到这个声名鹊起的
草民的上书,史称《上孝宗皇帝第一书》。
十年前的《中兴五论》,还没递到他
手里,大概就被一群政见不合的臣子给,雪藏了。
此时龙颜大振:“欲榜朝堂以励群臣”。
而丛林中生存的野狐,最能嗅得风的走向,
当曾觐来访,他跳墙而遁时,应已心知未来将福祸难依。
至此八日后,二次上书,宰相赵雄携人来询——
在一个草民,睥睨人寰、纵论天下的神气中,
历史揣摩着“安于一隅”的成语,赵雄揣摩着
“庸愚龌龊”四个字和政治利弊,
不动声色的皱了皱眉头,结局已悄然注定。
又十日,第三次上书,宋朝南渡以来,
最震惊临安府的事情发生了——
“给个官当当,考察一下”,皇帝如是说;
仿佛某种自尊心的受挫,他忽地跳起来,
——嗟来之食,当弃之如敝屣。
“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
以博一官乎?”陈亮说。
(此时是否有另一种可能?他或许也暗知
朝堂潜藏的派系之争,和自我脾性的不适宜,
合则出,不合则隐;远遁未必是坏事。)
——渡江而归时,有七八条猛龙在胸膛里憋屈打转。
醉了,醉了,趴在乡下的月牙桌上,
趴在酒杯和梧桐树的叶影的婆娑声里,
趴在喧嚣和寂静之间,
任性地打出响彻云天的呼噜声,
一袭白衣肩胛斜耸,像只高傲的鹮。
此后。又是个十年过去了,高宗死于临安,金使节来吊,
态度傲慢;慨怒间,忘了此时已身负过两次命运
的牢狱之灾的碾压,垂垂老矣。当第四次上书,
高呼复仇时,凝滞的水塘里,
激起的最高浪花上,只不过是被朝堂复缀了狂怪之名。
五、文谈天下
命运在遍布沼泽的森林里提着黑漆皮灯笼踯躅缓行,
理想在冬雪后的天空中释放寂灭气息,偶见
落单的
鸿雁踞在雪堆上泣血挽唱,
或,波涛汹涌的爱河里流卷礁石的浪峰上偶有鱼鳞闪烁,
思想的酒杯里即使盛满月光,一杯下去也难浇心中块垒。
“落魄醉酒,与邑之狂士饮”,在陈亮贬斥权贵时,
没意识到,臭狗屎一样的黑糊糊的苍蝇专门捕捉
风声里飘来的圆形马蹄铁上沾染的气味的平仄。
刑部尚书何澹的皮鞭,狠狠抽在了文人的风骨上,
喊没喊疼不知道,但被放出时,
应该庆幸当初翻墙而遁,渡河而归。
使得身份救了一命。
第二次蒙冤又活命的细节,他已忘记。
只将胸中乾坤,腹中日月,付诸笔下。
思想上的对手是铁与磨刀石之间的互相隐喻;
擦出的,是谁额头上的荣耀,或汗渍?
由此出发,朱熹与陈亮的辩论持续了十多年。
书信往返于乡野和朝堂之间——
人中之龙在历史的肩膀上蹬一脚,
文中之虎在历史的屁股上踹一脚,
远远的对视中,有一匹奔跑的马,从纸张的
地平面上,旋转于视线的中心:
(——它的方向感和速度主要由纵横驰骋的心,还是由
马背上的骑手用缰绳去提拽?或者,可能,都需要?)
天空与地面之间合出一片静默——
鹰能不能解释熊的撼山之力?
熊能不能解释鹰的飞行之能?
——道,在飞行里还是在行走中?
——但目光与目光之间对视而迸出的闪电,
使南宋百姓充分尊敬了,英雄的文韬武略。
以家乡为名的学派,足以傲立时间的洪流。
只是,胸膛里翻滚的报国情怀,总是无处宣泄。
书籍的岛屿上,有船只停泊,有马尾在青草上轻轻扫过。
思想的深海里,鱼与珊瑚皆是绝句,留存千古文章化石。
六、珠零玉落
此时,距离上书《中兴五论》,已过去了,两个十年。
此时,距离第二次上书之后渡河而归,潜心学问,
与朱熹书信往来间进行旷世辩论,又一个十年。
此时,距离两次牢狱之灾之后,又一个十年。
此时是,第三次上书无果之后的,第三次入狱,
复经受三年酷刑鞭笞。人生有多少个十年?
走出牢房时,更觉风雪寒凉,垂垂老矣,
立于危崖悬冰之上,茫茫然四顾,竟似举世皆敌。
“百世寻人犹接踵”,他想起:“但莫使、伯牙弦绝!”
嘴角微露笑意,胸膛顿时暖和:稼轩知我!
那是他们早期的相识,剑光忽闪间过桥而来,
强壮的汉子一掌掀翻劲马,大踏步行走,
竟不肯做半分停留;长长的背影烙在黄昏的石拱桥上,
被窗内的辛弃疾惊奇的收入眼中。
脾气总和志向有关,壮志难筹时的金戈铁马
都缩进胸膛与热血押韵,更是沉郁顿挫。
(——我最怜君中宵舞,
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
——天下适安耕且老,
看买犁卖剑平家铁!壮士泪,肺肝裂!)
忆起与稼轩同游鹅湖,十里长松夹道相迎,
又雪中煮酒、林中高歌、论兵天下,
碰盏间,正有百万雄兵在酒杯飞溅起的
浪尖上左右穿插,横渡长江而去收复河山。
几杯烈酒下肚,思起“纸上谈兵”、“百无一用
是书生”,又不觉双双抱头,嚎啕大哭。
相见恨晚,依依惜别,千言万语难尽,
想起归程,雪深泥滑,稼轩骑马一路追至鸬鹚林,
郁郁而归。不觉湿了眼眶:“树犹如此堪重别。”!
而此刻,站在被命运磨盘碾压过的铜豌豆的齑粉堆里,
站在盛满黑糊糊的骨头碎渣的生活的碗里,
站在不胜唏嘘的知天命之年,
想着老朋友,也想着思想上的老对手,
想到此刻:这个钦点的状元郎,终是得来的太迟了。
即使现在已暗知胸中文韬武略远远比不上,
对新旧皇帝间的父子关系说句好话有用,
——却也无话可说。
正振奋精神,欲伸展平生报国之志,
背部的鞭痕忽然隐隐作痛,牢狱里受的内伤更与何人纷说?
呜呼哀哉!弥留之际不免思及,一生之垂范:诸葛亮。
想来远赴冥漠之乡,自有灵幡带飘、
星星扬月行军,银河簇拥浪峰: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一介布衣,一生从未做过南宋半个官。
而今长风浩荡。只有,只有——
“文以载道”、“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
宁用以博一官乎?”……
——铿锵的元音响在历史的长歌中。
璨若星河的民族英豪们曾经说过:
文人的情怀,是真正坚硬的东西,
仰望它,须把头颅高高昂起,挺直腰脊。
《击壤》
那是一个高手,像一尊完美的力学体雕塑,
他替时间和回忆延续着某种:存在和气韵。
——半蹲在地上,蜷曲腰背,蓄势如弩弓,
脚趾扣地,脚踝后半截虚抬着,
整个筋骨都似要发出“咔咔”的响动来。
背部的骨肉线条,紧贴着呼吸微微晃动,
强韧而谐和,像随海的暗涌起伏的波浪,
一直延续至腹部。(有时背对着我喃喃低语,
有时沉默如梵寂的磨盘。)他把玻璃弹珠牢牢夹在:
右手大拇指和食指中节构成的喙型几何图案里。
童年时,他曾无数次出现在我梦里,又被一脚踹出去。
我的高、高年级同学,他曾挫败过我。
梦中心理阴影面积,集中在这个游戏的关节处,
予以我狠狠一击:就像他把玻璃弹珠
以“丹田之气”,猛地发射出去,迅速又精准。
三十年后,当再次遇见他,他已是个成熟诗人,
着实令人恍惚,作为仇敌和同行,我曾在,
酒桌上礼貌地和他握手,一边忍耐他笑着
唠叨玻璃弹珠:指尖的螺旋力,时间掌控,
几何运动,呼吸起伏,或关于精确、感知。
高超的技艺是否可以创造一切?
精准与否,击中与被击中,道与术。
——或者,光明与黑暗?
玻璃弹珠与《击壤歌》里飞来的壤,相隔几千年,
本质依然是:技艺里,物的不同形态。
大小尺寸,方与圆,决定了它的重心所在,
而所需要的游戏技巧,大概、可能——
同与不同,取决于跨时空:人类精准感知所把握的趋向。
那个击壤的远古活动,他或许不一定能游刃有余。
就像他谈起艺术,谈起冥思,谈起丹田之气,
谈起赋予。“击中”与文学是不是像个类同游戏?
这一切我已不愿思考:受限于舌头的管辖,
手艺人有手艺人必须沉默的部分。
而关于技术层面的争论,由物到诗,
由时间到空间,似乎毫无意义,又似乎意义深远。
一半是对阴影面积的正视,一半是保持友善的沉默距离。
很多年过去了,敌手已在黑暗中缓缓隐去面庞,
我写下这首诗,是试着捞出他、并与自己握手言和。
昭君出塞
细察时间的鸦群落于公元前某个遍插刀剑的历史悬壁上,
而后扭动着文史的小屁股一溜烟爬进贪婪的洞窟,
想象一滩墨汁随沉默着的宫廷画师沉默着的毛笔沉默落下,
纤维纸皱褶成一轮浅月、升出浓重得阴影,
嵌入红墙碧瓦、凝固的深井。在汉史,在帝王的半张残面。
不懂贿赂的宫女不是个好宫女:美人儿安静。
淡眉上的望穿秋水安静,静如幽宫闺房的一抹清香。
宏伟的宫殿更安静。
安静地听不到哪怕半根银针坠地的声音,
只有风在雕龙的檐角嘶吼,与野外猛兽的咆哮声合韵。
阵风吹过西汉摇曳着的青铜、花朵,吹过长安城外,
阴山下,两个庞然大物的默契正合力撞出,一片
纁袡前的静默,如一只人手在无声的花丛中胡乱游走,
美,在两只巨兽耳鬓厮磨的口水直流里吐出花容,
美,又如风云的浪尖猛烈撞击,晃悠着荡出明月。
她的牙齿洁白如羔羊,她的脸蛋伴着诗经,
美得如此惊心动魄——
她的手指,纤柔如烽烟的韵尾袅袅着飞天的舞姿,
她的细腰,娇嫩如空谷幽兰秋水共一色长天风华,
自请汉婿的老单于只一眼便深深沦陷于她的美。
民女可做公主被赐予,——唯有美是永恒而高贵的。
自此,历史的色彩的编钟就:在捡了便宜胡子拉碴的
呼韩邪,满心欢喜跪拜谢恩山呼万岁的恢宏大殿;
在回声高悬的漩涡里:被后世文人墨客们反复敲击,
荡出一层又一层或庄严,或咸涩的光晕。
在祖孙三代穹庐似的羊毛毡帐里读书弹琴,在暴力之美
和香甜的体液中流放仁慈的和平——
在呼伦贝尔草原奔驰的马鞍上缝纫羊皮袄子,
在烽烟之妖的尾椎骨之下,撒下粮食的种子,
缀着彩虹和浓烟的,半个世纪的动乱:结束了。
想象一朵报春花儿随草原的敬意隆成一座翠玉的青冢,
任凭历史举日月之眸:去赞美、去沉沦或遐想;
唯有一群思乡的大雁驮着山川和河流,归来一翅沉重的美。
纪一·爷爷的烟斗和茶
昏暗的灯光,老屋,五个老兄弟
正对门,黑漆油旧的桌柜
墙上挂着幅模糊的画
记不清了,总之是个人形
二爷和三爷,桌柜两边坐着
四爷在西墙边的凳子上坐着
还有些什么家具,也记不清了
不过,人是齐的
五爷在东炕裹着被子坐着
炕沿中间是盘膝的爷爷
黑旧袄子,旱烟袋
圆顶带扣的帽子
铜烟斗很长,在爷爷手里
烟锅里,火星一闪一闪的
爷爷的前面有个火炉,炭火通红
一口茶杯,也是黑底的,粗铁丝缠着杯口
铁丝扭缠在一起,炕沿上放着
热气腾腾,还有熬得吱吱作响的茶
这些,屋里独自玩耍的我记得最清楚
在我心底一坐就是近三十年
因为爷爷很厉害
只有他有大烟斗,戴帽子
坐在火炉旁熬茶
纪三.童年的秋天
那些童年的秋天
连趋回的念头
都荡着阳光暖暖的舒软
是铺满蜜膏稠稠的幸福小路
送我赤脚,扑向那个金色海洋
那里,她用层层温柔的暖,把我浮起、浸泡
那里,每一束稻穗都是温暖的浪花
那里,每一粒稻籽都迸着金色的闪电
二十多年前,她给我捎来爱的信笺
让我翻开童年,就无比幸福
时间,随着太阳的羽毛
舒卷在那片田野
微风,走进辽远的稻田
马车,隐现在蜿蜒的小路
人们,漫散在金色的海洋
在那遥远的边疆,金色的大山托起太阳
偎依着他的黄河,恬静的躺着
她那温柔的眼眸,波光粼粼
她那红柳和芦苇的楚衣
迷倒了我的童年
想说她是我的梦中情人
又怕大山不答应呀
一只蜻蜓,落在我尖尖食指二十多年
蜻蜓的一只复眼
看见了父亲的镰刀,母亲的头巾
而我,痴迷于它透明的薄翼
像我童年手指上,翩跹的那一双
阳光,也被它们舞的轻盈
我喜欢它们那细小纤足落在手指的感觉
轻轻的,柔柔的,痒痒的
如我自己,欢快在松软的稻田
看天空,阳光温暖的地方
燕子,轻唱着蔚蓝的欢欣
看海洋,浪花跳动的地方
野鸭儿、麻雀儿、稻草人,他们
驮起金色喜悦,扑向太阳的流光
他们,偶尔也会看见我、看见我
在父亲和母亲用镰刀劈开的金色港湾里
我可能拿着稻秆,与几只蚂蚱嬉戏
也可能正在拣起一只湿漉漉的蜗牛
可能在地的埂上看些渠沟里的青蛙和小鱼儿
或者,一只金甲虫猛的飞起,我欢快追逐
或者,可能……
更多的时候,我坐在稻捆上
伸出手指,等一只蜻蜓落下
就像等父亲的一声吆喝:“背稻子了”
《怅惘之伤——》
一.
天地狂逸不羁,啸尽烟霞
戈壁放浪形骸,狂歌醉舞
——是谁
枕着月光入眠
可是那健峭傲岸的雪岭
怅惘,一棵岁月的树翘首长叹
浮光天际,青鸟盘旋低吟
秋来了,长袖挥落一地幽残
风冷了,诗瘦了
月好美,我想抱一抱她
二.
冷月哀弦惊的山幽谷静
花丽情柔 叶枯黄
一夜纷乱 孤星涔涔泪
山不知山,水不知水
落叶不解秋风意
我本空山独酌
忽听月泣幽怨凄凉
秋没有哭,只是伤悲
一场心雨,带着那个叫雨的女孩
——淋漓
新西兰 澳纽网出品
编辑:小图
1,401 view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