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长篇连载 > 第十五章
作者: 安齐名 人气: 日期: 2005/2/21 0:12:30
所谓灯红酒绿,或许只是随着心情的不同,一种被眼睛欺骗了的繁华吧。
今天的skytower,通体碧绿的象翡翠一样,高高地插进漆黑的云层中,老甘仰着脑袋看着,羡慕的表情溢于言表。
“安子,你还真别说,天天远远地看着,这只有到了跟前,才能看出来有多漂亮啊。”
我看着老甘砸着嘴巴的样子,想起了大海那天那句滑稽的“各位,欢迎你们到奥克兰来”。我并不惊诧于老甘的赞美,下了飞机的人,没有人不会为这个瑰丽的城市所感慨,然而自从我真正踏入其中的时候,我才真正的看清楚了这个城市,看清了奥克兰有多美,也看清了奥克兰有多丑。
而老甘,也只是刚刚看到它的美丽而已。
“安子,你看它象不象一把宝剑,正好插在奥克兰的心脏上。”
“别做梦了,你他妈看过绿色的宝剑么?”
我拉着老甘钻了进去。
我不止一次地来到skycity赌钱,但我始终牢记着大海告诉我的话,一切都只是游戏,玩玩可以,但不要当真,在赌场流连的日子里,我亲眼看到了几十万 纽币瞬间付水东流的悲哀,也看到了小女孩偶然压中了treblesix赢到了一张回家的往返机票的开心,喜喜悲悲见得多了,眼前的事情就象看电影一样,我 已经没有一点的感觉了。
“goodluck,sir(先生好运)”侍者递给我20钮币,我笑了笑。
我笑呵呵地把筹码放在手里,天蓝色的小圆片,摞成一排挺好看的,我得意得笑了笑,又放了10块钱到桌子上。
“安子,玩什么呢?这么开心!”老甘灰头土脸地坐在了我旁边。
“锄大地啊?”我看了看手里的牌,有三条J,又得意的笑了。
“bet?(压吗)”
“ofcourse。(当然)”我放上去20块钱。
“牌这么好,怎么就压这么少啊?”老甘趴在我耳朵边上问。
“因为我第一次只压了10块钱啊。”我坦然地看着侍者翻开手中的牌,“操,竟然没有A,K,可真他妈幸啊。”
老甘看着30块钱又递回到了我的手上,“怎么,没赢到钱吗?”
“对咯。”我漫不经心地玩弄着手里的筹码,又拈了10块钱放在了上面。
“我操。安子,你在这磨手指头那?”老甘摇了摇头,“你这得什么时候才能赢到钱啊。”
“这不是已经赢了么?”我笑着抖着手里的筹码,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我已经赢了快100块钱了,有的时候不一定要赢钱才能开心。”
老甘眼巴巴地看着我:“我就没那么幸运了……刚刚本来赢了400块,结果最后一把都压上了……你那还有钱了么?”
“老甘。”我示意侍者不用再给我派牌了,“别怪兄弟不够意思,赌场里可是没有借钱的规矩,一切都得靠自己来赢。”
“操,咱俩还扯这个……”老甘情绪明显有些低落。
“好啦好啦。”我搂着老甘的肩膀,“一会带你去看showgirl,免得说兄弟不仗义。”
“showgirl是啥?”
“去了你就知道了。就你这逼样,肯定以后就是常客了。”
说实话,来到奥克兰这么长的时间里。我还真的没有去过所谓的showgirl。几天来烦躁的心情一直让我郁郁不乐,今天正好去发泄一下。
“快看,快看,马上要脱光了!”
老甘从一进来就没停过,不挺地在喊,我的耳朵都快疼了。
小小的舞台上,饶着钢管转来转去的那个女孩卖力的扭动着身体,那团甩来甩去的黄毛,一对象气球一样蹦来蹦去的乳房,晃了我头晕眼花,身边的人都着迷似的叫嚷着,夹杂着尖利的口哨声。
灯光虽然昏暗,但墙上的NOSMOKING还是很清楚,我侧过身去,把目光从那个一丝不挂的裸体上挪开,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没有一丝冲动,我只感觉我的面前有团肉在嘈杂的声音里滚来滚去,我想起了那天晚上的那个白人,突然很恶心……
我叫了一杯啤酒。
“怎么啦你?”老甘凑了过来,“这么过瘾的你都不看?”
“老甘,”我摇晃着瓶子里的酒,欣赏着灯光下的那团琥珀色,“如果有可能,你会选择什么样的死法?”
“什么?”老甘莫名其妙的看着我,“你发烧了吧你。”
“我是说真的呢!”我仰头把酒一饮而尽,“我觉得活在奥克兰挺累的。”
“切,”老甘的表情告诉我,他一定觉得我现在神经有问题,“累?我他妈在这儿的这两天,过的象天堂似的,自己有的时候都不敢相信这些事实。我可不象死。”
又一个女孩走了出来,老甘不再理我了。
“如果有可能,你会选择什么样的死法?”
这个问题最开始是大海在Magreata问出来的。
我记得我选择的是吞枪,因为我觉得这样的死法只是一瞬间的事情,没有一点痛苦;Fanny选择的是安乐死,她说她希望死了之后还是这个样子,到了天堂都依然美丽;成亮选择的是服安眠药,他的理由是……这样死的几率最小。
大海笑着说我是英雄主义者,Fanny是完美主义者,而成亮则是个不折不扣的机会主义者。
所以我们都很感兴趣他想怎么死。
“如果我真的走投无路了,我会选择跳楼。”
“为什么?”Fanny很奇怪,“我站在高的地方一定不敢跳下去。”
“因为……那是一种真正的解脱,”大海当时的神情我记得很清楚,和我现在几乎一个样子,眼睛呆呆地盯着啤酒杯中的泡沫,“谁站在高得地方都会害怕的,越 高就越害怕,但是如果当一个人去选择死亡的时候,他就必须要克服这道最后的障碍。看着脚下的深渊,听着身边呼啸的风声,如果你害怕了,你大可以退回来,继 续着你不值得再继续的生活……”
“那你才应该是英雄主义者啊?”我笑着插了一句。
“真正敢于选择死亡的人是不怕死亡的,”大海摇 了摇头,“当你闭上眼睛,向下跳的时候,脑袋里一定会有一个很清楚的念头:这,是我人生的最后一步了。很可笑……我想知道人在走完人生最后一步的那段日子 里,也就是当你纵身跳下去到你落到地面前的那段时间里,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在后悔。”
那个时候,我,Fanny,成亮都没有说出话来,我想他们两个人想的一定和我一样。
如果换作我们,我们会不会后悔,我们会后悔什么?
我不知道Fanny和成亮会不会也和我一样在想自己为什么来奥克兰。
大海不会常常把这样有哲理的话放在嘴边,其实我们也都更习惯整天风风火火,骂骂咧咧的他,所以直到他静静地吐出最后一字,我才小心地端起了杯子。
那些本来就很有分量的话,从大海的嘴里说出来,更重了。
“安子……”老甘推了推我,“你究竟怎么了?”
“我?”没什么,”我坐正了身子,“老甘,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会来这里。”
“我……”老甘沉思着。
我笑了,其实我们大家都一样,谁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来这里,谁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那个高中的时候发誓要到美国去看现场的NBA比赛的小孩子有多 么的可笑,我想如果我没有来奥克兰,现在不是在showgirl里看脱衣舞娘的表演,而是在现场看奥尼尔的大力扣篮,我一定还会问自己为什么来美国的。
我终于明白了在piha的那天晚上,我一直不明白的事情。
大海说自己没有作为的原因和我一样,我们都过着同样混乱而无目的的生活,奥克兰就象一个巨大的磁场,当我们不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被吸引过来,而当我们走进来的时候,才发现所有的指南针都在瞬间失去了方向。
我长长的叹了口气,叹给我在奥克兰得到的18万美金和失去的我的生活。
“老甘,我不想看了……”
“啊?”老甘面有难色地看着我。
“没什么,”我站起了身,“我出去走走,你自己慢慢看吧。”
我在皇后大道上缓缓地溜着车,本来打算借着带老甘出来玩的机会让自己心情变的好一些,可突如其来的那些想法,让我本来就低落的心情更是跌到了谷地。
象一只兜来兜去总要回到蜂巢的蜜蜂,我发现我最后还是停在了大海的厂子前。
夜暮下的David’sshop,依旧没有灯光,没有人影,死气沉沉。
我拨了拨大海的电话,没有反映。
“妈的!”我靠在车门上,掏出只烟叼在嘴上,“这小子这么记仇……”
我的手在兜里翻打火机的时候,摸到一张纸片。
是一串号码。
小凡留给我的号码。
“Nexttime,pleasecallmeSally……”小凡放浪的表情又历历在目,我打着了火机,看着那张纸片冒出了一股呛人的黑烟,焚化在我的脚下。
那天打在大海脸上的右拳,似乎在隐隐作痛。
“大海,对不起……”我默默地对着我的右手诉说着,“其实我和小凡已经成了陌生人,我只是不想让她走一条本来不属于她的路……”
“大海……如果你已经原谅我,就快点出来吧。”
“喂!”
我猛地抬起头。
不是大海,站在我面前的是三个年纪轻轻的男孩,看上去不过18,9岁,叼着烟卷,染着花俏的头发,吊儿郎当地样子让我想起了成亮。
“什么事儿?”我的手揣进了裤兜里的钱包,小心翼翼地注视着眼前的三个不速之客。
为首的一个卷头发,穿皮甲克的男孩靠近一步,神秘兮兮地看了一下四周。
“要粉儿吗?”
原来是卖毒品的小混混儿,我的心放松了些,手也拿了出来。大海曾经和我说过,在奥克兰贩卖毒品的小孩儿都是最低层的混子,绑架,抢劫,杀人,放火是轮不到他们干的。
“不要!”我厌恶地看着面前那张还略显稚嫩的小脸儿,还有那条挂在脖子上的链子,在月色下反着光。
“这个呢?”他看来并不死心,又掏出来一个小塑料袋,里面装几颗白色的药丸,“保证你high到极点,便宜……”
“不要!”我拉开了车门,准备离开了。
那个男孩很失望的把摇头丸放回了口袋里。
妈的,冤不得现在老外叫我们垃圾,我突然都有了一种很丢人的感觉。因为我和他们同样的皮肤,同样的面孔,同样的语言。
我看到有个男孩突然拉过那个卷毛耳语了几句。
他又走了过来。
我警惕地看着他,琢磨着刚刚那小子在和他说了什么。我身边完全没有可以防身的家伙,没有路过的行人。
妈的,大不了拼他个鱼死网破。
我攥紧了拳头。
“大哥。”他瞄了瞄我,又看了看我身后的车,“你是在那家店买的车吗?”
“车?”我有点惊讶,“哪家店?”
“David’sshop。”他指了指大海的店,“很多中国人的二手车都是在那里买的,你这个呢?”
“你问这干什么?”我看了看黑咕隆咚的David’sshop,心里顿生犹疑。
那天从大海家一怒出走后,我把钥匙也扔还给了他,后来在一个日本人手里花5000钮币买到的现在这辆红色的nissan跑车。
“到底是不是啊?”卷毛好象对这辆车的历史很感兴趣。
我记得曾经有个朋友给我讲过一件事情,他花4000块买了一辆二手的黑色nissan跑车,性能一般,也就是凑合着开着。但是有一次他的兄弟和另一帮人 参与了一次规模很大的斗殴事件,当他开着车赶到那里的时候,竟然意外的发现所有的人都停下了打架。原来这小子狗屎运,那辆车曾经是14K的一个老大很长时 间前开过的车,几经转手到了他手上,结果人虽然不在,就靠着一辆破得不能再破的二手车,一场惨烈的打斗没有继续下去,大家还在一起吃了顿饭。交了朋友。
莫非我的运气也这么好?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车子。
“是不是啊?”卷毛不停地催我。
“是!”我说了句假话,“怎么啦?”
“那你拣便宜了!”
“什么?”
“给我20块钱,告诉你个天大的秘密。”
“20块钱你们三个人怎么够分呢?”我笑着拿出了30钮币,“有什么就快告诉我吧。”
卷毛接过30块钱,分给了另外两个人每人10块,咧开嘴巴,脸上突然露出了孩子般天真的笑,让我想到小的时候过年多分到了一块糖果的傻样。
刚刚我还在防备着和这样一个孩子进行一场撕打,我都忍不住笑了。
“你知道吗?这家店的车有问题!”
“问题?”我的笑凝固住了,“什么问题?”
“车的里程数是调过的。”他煞有介事地比画着,“这辆车花了你多少钱?4000还是5000?其实也就值2000块钱……”
“你他妈听谁说的?”我一把把卷毛抓了过来,突如其来的被人拎了起来,卷毛吓的把钱掉到了地上。
另外两个孩子也没有想到我突然的暴怒,呆呆地看着我们。
“我听……听别人说的……”
“别人?”
“是啊,东区很多人都在这里买车,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明天要找老板来算帐呢……”
我放下了卷毛,落地的一刹那,他和另外两个孩子飞似的跑掉了,我注视着三个小小的身影钻进了黑夜里,心里陡然变得沉重起来。
电话突然响了,是Fanny。
“Michael,你怎么还不回来?”
“大海的店……出事了……”
“……”Fanny停顿了半晌,“很晚了,先回来吧,明天早上我们一起过去。”
挂了电话,我又拨了次大海的手机。
依旧没法接通。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抬起头。
可是宁静的夜色没有给我丝毫回答,只有一闪一闪的星星在看着我,好象在看一场他早就知道答案的闹剧。
今天的skytower,通体碧绿的象翡翠一样,高高地插进漆黑的云层中,老甘仰着脑袋看着,羡慕的表情溢于言表。
“安子,你还真别说,天天远远地看着,这只有到了跟前,才能看出来有多漂亮啊。”
我看着老甘砸着嘴巴的样子,想起了大海那天那句滑稽的“各位,欢迎你们到奥克兰来”。我并不惊诧于老甘的赞美,下了飞机的人,没有人不会为这个瑰丽的城市所感慨,然而自从我真正踏入其中的时候,我才真正的看清楚了这个城市,看清了奥克兰有多美,也看清了奥克兰有多丑。
而老甘,也只是刚刚看到它的美丽而已。
“安子,你看它象不象一把宝剑,正好插在奥克兰的心脏上。”
“别做梦了,你他妈看过绿色的宝剑么?”
我拉着老甘钻了进去。
我不止一次地来到skycity赌钱,但我始终牢记着大海告诉我的话,一切都只是游戏,玩玩可以,但不要当真,在赌场流连的日子里,我亲眼看到了几十万 纽币瞬间付水东流的悲哀,也看到了小女孩偶然压中了treblesix赢到了一张回家的往返机票的开心,喜喜悲悲见得多了,眼前的事情就象看电影一样,我 已经没有一点的感觉了。
“goodluck,sir(先生好运)”侍者递给我20钮币,我笑了笑。
我笑呵呵地把筹码放在手里,天蓝色的小圆片,摞成一排挺好看的,我得意得笑了笑,又放了10块钱到桌子上。
“安子,玩什么呢?这么开心!”老甘灰头土脸地坐在了我旁边。
“锄大地啊?”我看了看手里的牌,有三条J,又得意的笑了。
“bet?(压吗)”
“ofcourse。(当然)”我放上去20块钱。
“牌这么好,怎么就压这么少啊?”老甘趴在我耳朵边上问。
“因为我第一次只压了10块钱啊。”我坦然地看着侍者翻开手中的牌,“操,竟然没有A,K,可真他妈幸啊。”
老甘看着30块钱又递回到了我的手上,“怎么,没赢到钱吗?”
“对咯。”我漫不经心地玩弄着手里的筹码,又拈了10块钱放在了上面。
“我操。安子,你在这磨手指头那?”老甘摇了摇头,“你这得什么时候才能赢到钱啊。”
“这不是已经赢了么?”我笑着抖着手里的筹码,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我已经赢了快100块钱了,有的时候不一定要赢钱才能开心。”
老甘眼巴巴地看着我:“我就没那么幸运了……刚刚本来赢了400块,结果最后一把都压上了……你那还有钱了么?”
“老甘。”我示意侍者不用再给我派牌了,“别怪兄弟不够意思,赌场里可是没有借钱的规矩,一切都得靠自己来赢。”
“操,咱俩还扯这个……”老甘情绪明显有些低落。
“好啦好啦。”我搂着老甘的肩膀,“一会带你去看showgirl,免得说兄弟不仗义。”
“showgirl是啥?”
“去了你就知道了。就你这逼样,肯定以后就是常客了。”
说实话,来到奥克兰这么长的时间里。我还真的没有去过所谓的showgirl。几天来烦躁的心情一直让我郁郁不乐,今天正好去发泄一下。
“快看,快看,马上要脱光了!”
老甘从一进来就没停过,不挺地在喊,我的耳朵都快疼了。
小小的舞台上,饶着钢管转来转去的那个女孩卖力的扭动着身体,那团甩来甩去的黄毛,一对象气球一样蹦来蹦去的乳房,晃了我头晕眼花,身边的人都着迷似的叫嚷着,夹杂着尖利的口哨声。
灯光虽然昏暗,但墙上的NOSMOKING还是很清楚,我侧过身去,把目光从那个一丝不挂的裸体上挪开,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没有一丝冲动,我只感觉我的面前有团肉在嘈杂的声音里滚来滚去,我想起了那天晚上的那个白人,突然很恶心……
我叫了一杯啤酒。
“怎么啦你?”老甘凑了过来,“这么过瘾的你都不看?”
“老甘,”我摇晃着瓶子里的酒,欣赏着灯光下的那团琥珀色,“如果有可能,你会选择什么样的死法?”
“什么?”老甘莫名其妙的看着我,“你发烧了吧你。”
“我是说真的呢!”我仰头把酒一饮而尽,“我觉得活在奥克兰挺累的。”
“切,”老甘的表情告诉我,他一定觉得我现在神经有问题,“累?我他妈在这儿的这两天,过的象天堂似的,自己有的时候都不敢相信这些事实。我可不象死。”
又一个女孩走了出来,老甘不再理我了。
“如果有可能,你会选择什么样的死法?”
这个问题最开始是大海在Magreata问出来的。
我记得我选择的是吞枪,因为我觉得这样的死法只是一瞬间的事情,没有一点痛苦;Fanny选择的是安乐死,她说她希望死了之后还是这个样子,到了天堂都依然美丽;成亮选择的是服安眠药,他的理由是……这样死的几率最小。
大海笑着说我是英雄主义者,Fanny是完美主义者,而成亮则是个不折不扣的机会主义者。
所以我们都很感兴趣他想怎么死。
“如果我真的走投无路了,我会选择跳楼。”
“为什么?”Fanny很奇怪,“我站在高的地方一定不敢跳下去。”
“因为……那是一种真正的解脱,”大海当时的神情我记得很清楚,和我现在几乎一个样子,眼睛呆呆地盯着啤酒杯中的泡沫,“谁站在高得地方都会害怕的,越 高就越害怕,但是如果当一个人去选择死亡的时候,他就必须要克服这道最后的障碍。看着脚下的深渊,听着身边呼啸的风声,如果你害怕了,你大可以退回来,继 续着你不值得再继续的生活……”
“那你才应该是英雄主义者啊?”我笑着插了一句。
“真正敢于选择死亡的人是不怕死亡的,”大海摇 了摇头,“当你闭上眼睛,向下跳的时候,脑袋里一定会有一个很清楚的念头:这,是我人生的最后一步了。很可笑……我想知道人在走完人生最后一步的那段日子 里,也就是当你纵身跳下去到你落到地面前的那段时间里,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在后悔。”
那个时候,我,Fanny,成亮都没有说出话来,我想他们两个人想的一定和我一样。
如果换作我们,我们会不会后悔,我们会后悔什么?
我不知道Fanny和成亮会不会也和我一样在想自己为什么来奥克兰。
大海不会常常把这样有哲理的话放在嘴边,其实我们也都更习惯整天风风火火,骂骂咧咧的他,所以直到他静静地吐出最后一字,我才小心地端起了杯子。
那些本来就很有分量的话,从大海的嘴里说出来,更重了。
“安子……”老甘推了推我,“你究竟怎么了?”
“我?”没什么,”我坐正了身子,“老甘,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会来这里。”
“我……”老甘沉思着。
我笑了,其实我们大家都一样,谁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来这里,谁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那个高中的时候发誓要到美国去看现场的NBA比赛的小孩子有多 么的可笑,我想如果我没有来奥克兰,现在不是在showgirl里看脱衣舞娘的表演,而是在现场看奥尼尔的大力扣篮,我一定还会问自己为什么来美国的。
我终于明白了在piha的那天晚上,我一直不明白的事情。
大海说自己没有作为的原因和我一样,我们都过着同样混乱而无目的的生活,奥克兰就象一个巨大的磁场,当我们不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被吸引过来,而当我们走进来的时候,才发现所有的指南针都在瞬间失去了方向。
我长长的叹了口气,叹给我在奥克兰得到的18万美金和失去的我的生活。
“老甘,我不想看了……”
“啊?”老甘面有难色地看着我。
“没什么,”我站起了身,“我出去走走,你自己慢慢看吧。”
我在皇后大道上缓缓地溜着车,本来打算借着带老甘出来玩的机会让自己心情变的好一些,可突如其来的那些想法,让我本来就低落的心情更是跌到了谷地。
象一只兜来兜去总要回到蜂巢的蜜蜂,我发现我最后还是停在了大海的厂子前。
夜暮下的David’sshop,依旧没有灯光,没有人影,死气沉沉。
我拨了拨大海的电话,没有反映。
“妈的!”我靠在车门上,掏出只烟叼在嘴上,“这小子这么记仇……”
我的手在兜里翻打火机的时候,摸到一张纸片。
是一串号码。
小凡留给我的号码。
“Nexttime,pleasecallmeSally……”小凡放浪的表情又历历在目,我打着了火机,看着那张纸片冒出了一股呛人的黑烟,焚化在我的脚下。
那天打在大海脸上的右拳,似乎在隐隐作痛。
“大海,对不起……”我默默地对着我的右手诉说着,“其实我和小凡已经成了陌生人,我只是不想让她走一条本来不属于她的路……”
“大海……如果你已经原谅我,就快点出来吧。”
“喂!”
我猛地抬起头。
不是大海,站在我面前的是三个年纪轻轻的男孩,看上去不过18,9岁,叼着烟卷,染着花俏的头发,吊儿郎当地样子让我想起了成亮。
“什么事儿?”我的手揣进了裤兜里的钱包,小心翼翼地注视着眼前的三个不速之客。
为首的一个卷头发,穿皮甲克的男孩靠近一步,神秘兮兮地看了一下四周。
“要粉儿吗?”
原来是卖毒品的小混混儿,我的心放松了些,手也拿了出来。大海曾经和我说过,在奥克兰贩卖毒品的小孩儿都是最低层的混子,绑架,抢劫,杀人,放火是轮不到他们干的。
“不要!”我厌恶地看着面前那张还略显稚嫩的小脸儿,还有那条挂在脖子上的链子,在月色下反着光。
“这个呢?”他看来并不死心,又掏出来一个小塑料袋,里面装几颗白色的药丸,“保证你high到极点,便宜……”
“不要!”我拉开了车门,准备离开了。
那个男孩很失望的把摇头丸放回了口袋里。
妈的,冤不得现在老外叫我们垃圾,我突然都有了一种很丢人的感觉。因为我和他们同样的皮肤,同样的面孔,同样的语言。
我看到有个男孩突然拉过那个卷毛耳语了几句。
他又走了过来。
我警惕地看着他,琢磨着刚刚那小子在和他说了什么。我身边完全没有可以防身的家伙,没有路过的行人。
妈的,大不了拼他个鱼死网破。
我攥紧了拳头。
“大哥。”他瞄了瞄我,又看了看我身后的车,“你是在那家店买的车吗?”
“车?”我有点惊讶,“哪家店?”
“David’sshop。”他指了指大海的店,“很多中国人的二手车都是在那里买的,你这个呢?”
“你问这干什么?”我看了看黑咕隆咚的David’sshop,心里顿生犹疑。
那天从大海家一怒出走后,我把钥匙也扔还给了他,后来在一个日本人手里花5000钮币买到的现在这辆红色的nissan跑车。
“到底是不是啊?”卷毛好象对这辆车的历史很感兴趣。
我记得曾经有个朋友给我讲过一件事情,他花4000块买了一辆二手的黑色nissan跑车,性能一般,也就是凑合着开着。但是有一次他的兄弟和另一帮人 参与了一次规模很大的斗殴事件,当他开着车赶到那里的时候,竟然意外的发现所有的人都停下了打架。原来这小子狗屎运,那辆车曾经是14K的一个老大很长时 间前开过的车,几经转手到了他手上,结果人虽然不在,就靠着一辆破得不能再破的二手车,一场惨烈的打斗没有继续下去,大家还在一起吃了顿饭。交了朋友。
莫非我的运气也这么好?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车子。
“是不是啊?”卷毛不停地催我。
“是!”我说了句假话,“怎么啦?”
“那你拣便宜了!”
“什么?”
“给我20块钱,告诉你个天大的秘密。”
“20块钱你们三个人怎么够分呢?”我笑着拿出了30钮币,“有什么就快告诉我吧。”
卷毛接过30块钱,分给了另外两个人每人10块,咧开嘴巴,脸上突然露出了孩子般天真的笑,让我想到小的时候过年多分到了一块糖果的傻样。
刚刚我还在防备着和这样一个孩子进行一场撕打,我都忍不住笑了。
“你知道吗?这家店的车有问题!”
“问题?”我的笑凝固住了,“什么问题?”
“车的里程数是调过的。”他煞有介事地比画着,“这辆车花了你多少钱?4000还是5000?其实也就值2000块钱……”
“你他妈听谁说的?”我一把把卷毛抓了过来,突如其来的被人拎了起来,卷毛吓的把钱掉到了地上。
另外两个孩子也没有想到我突然的暴怒,呆呆地看着我们。
“我听……听别人说的……”
“别人?”
“是啊,东区很多人都在这里买车,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明天要找老板来算帐呢……”
我放下了卷毛,落地的一刹那,他和另外两个孩子飞似的跑掉了,我注视着三个小小的身影钻进了黑夜里,心里陡然变得沉重起来。
电话突然响了,是Fanny。
“Michael,你怎么还不回来?”
“大海的店……出事了……”
“……”Fanny停顿了半晌,“很晚了,先回来吧,明天早上我们一起过去。”
挂了电话,我又拨了次大海的手机。
依旧没法接通。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抬起头。
可是宁静的夜色没有给我丝毫回答,只有一闪一闪的星星在看着我,好象在看一场他早就知道答案的闹剧。
声明:在澳纽网频道上发表的内容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的目的,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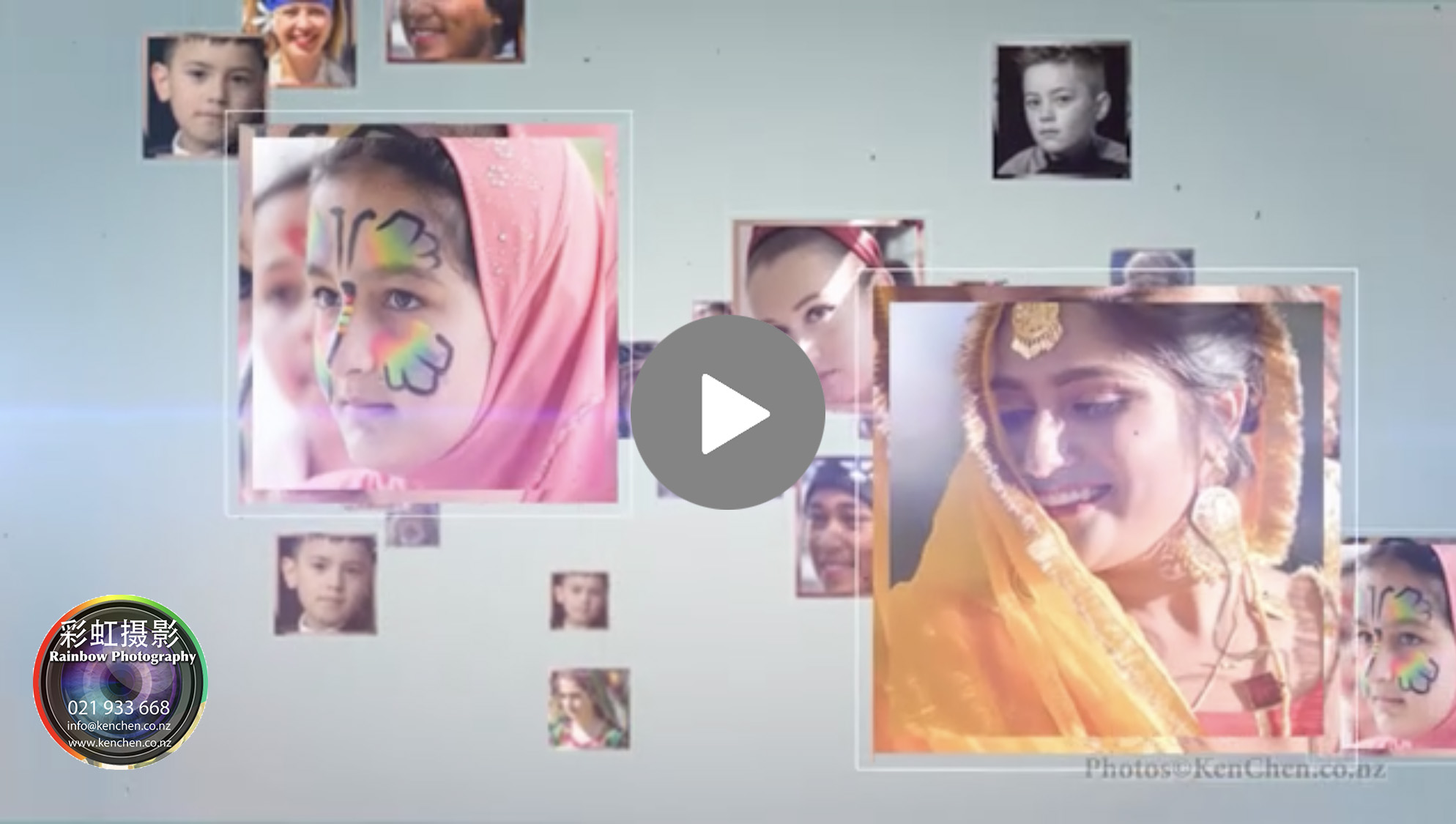


感谢您对澳纽网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