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新西兰旅游 > 被新西兰的繁花似锦震撼
人气: 日期: 2005/3/3
我童年生长在青砖石地、白墙玄瓦的江南水乡,看惯了陌上嫩桑,岸边翠柳, 墙头粉桃。加之从小爱描花卉,一本《花卉白描画谱》从头临摹到尾,画艺倒是没什 麽长进,但是能略识百草、初辨千花的。春赏芍药夏观荷,秋采黄菊冬探梅,当什麽 花木都不典型的季节交换之际,就向九溪跳跳蹦蹦过了那十八涧,竹径通幽便到了云 栖去看那些个在文人墨客笔下虚怀若谷、高风亮节的竹子。所有的这些学馀活动,都 是跟着目不识丁,生长在徐霞客游迹曾经到达,赞为“奇特是高僧”的雁荡山里,为 卖炭翁之养女,但却风雅无边的小脚老外婆。老外婆总是感叹说:千年花木啊,比人 更精怪。可我们居室太过狭窄,因此户外随着季节的赏花活动往往是不肯轻轻放过。 而那一方斗室里,老外婆总是在窗台上瓦钵栽上白色绣球花,入秋就团团簇簇地盛开 。船形的浅盆里,是来自樟州的水仙,请了园林局的高手,将拿水仙刀割成花苞挺立 而花叶下翻。而我的书案上,老外婆更是以水养着几咎草兰,伏案夜读时,千年的兰 香伴随着百年的石库庭院幽幽淡淡地飘着。时隔将近二十年,那故乡的沁人心肺的花 香常常梦幻般地突兀在我的脑海里,郁然趋之不散,挥之又至。
十一年前,外子先遣部队先开到纽西兰。并不喜花花草草的他,竟然在到达纽国的第一封信中,就欣喜若狂地向我汇报:“即便是我们江南人,也会被这里的繁花 似锦所震憾。我不认识那麽多种类的树木与花草,有些似曾相识,而又有些是从来没 有见过的,这些都有待於你来辨认。总之这儿鸟语花香……”我还开玩笑地对我那些 好朋友说:“‘鸟语花香’怕是听不懂那外国鸟说的语,即使鹦鹉学舌也绝不是国语 而怕是英语。而那花香是配备给老外的,我们中国人受用得了吗?”外子施展魅力, 好一阵“诱骗”,用无数的思念装点他的深情厚意以外,那似曾相识“孰能无情”之 草木也算是当了他的帮凶。我放下立志充当教师要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宏愿,傻乎乎 蒙懵懵来到纽西兰以後,知道外子的描述固然不差,而这儿的奇花异草连我这位外号 “李时珍”的,也只能识得五成。“鸟语”自是不在话下,每天清晨,都是被鸟儿呱 噪而从睡梦中惊醒,以为是在原始森林里度夜呢。而“人声”较之鸟语,却成了个稀 罕物。静谧、空旷、寥落、寂寞这个仿佛因为没有悠久历史创伤之感,而一派鸟语花 香如世纪初般纯净而不羼杂人世嘈闹的纽西兰,到底让我们这帮所谓追求自然美的人 有了返朴归真的去所了吧?
然而非也。这儿的千花百草,仿佛没有外婆置在我案头那几株小兰草显得有诗意 ;而这儿的花香万种,却使我害了让人坐立不安的“花粉”病。如今,正值冬去春来 ,百花齐放之季节,我家庭院那千馀平米的方圆里更是草花斗妍,特别是夹道数米的 水仙花,五彩缤纷,香气浓郁的让人有些头晕目眩,而我却是眼睛周际似乎有万根毛 绒绒小刺刺扎着不能直视人生;而鼻孔里奇痒无比,三五分钟就要恶狠狠地打喷嚏数 回地不能仪表万千;且时不时还眼中布满红丝,泪流满面,弄得三个儿子老问我:“ 是不是爸爸又在欺负妈妈?”我老跟外子说,纽西兰的一切都不如意,当了少数民族 不去说,英语算不得利落,工作也只能是自谋生路,比起中国的乡下妹进城打工好不 了多少。而那儿子在学校里,黑头发黑眼睛地混在里面总是没有大一统大汉族地光荣 感,连带了中国餐都宁愿饿到家里再吃,说是洋同学看到“这种饭”要笑话。好了, 如今连那春花秋叶也来欺生,都说新移民来了这儿十年八年後,多多少少是要患上这 种“富贵病”的。我寻遍洋大夫,总是给些洋扑儿敏之类的药吃,鲜能达到预期效应 ,倒是药性过强便昏睡,过後而头疼难忍,其结果是照样与鼻涕眼泪为伍;问那些个 个说起来神通广大的中国来的郎中,“临床经验丰富,手到病除”是否有偏方?回答 说:“特效药有一副,那就是整理行装,趁早打道归国,一切都会好。”啼笑皆非, 这种药方还用得着你来开?难道我们这种国产的“土人”,是根植不了这纽国的土地 之上?外子抗“病毒”有方,他浑然感不到花粉的厉害,对着泪眼涟涟衣巾湿的我, 一点同情之心都没有,说我是“无法享受自由空气”,说我是“挑剔之人自有恶报” ,“哪个让你整天对纽西兰不满的”?“再说开在中国的花儿与开在纽西兰的花儿到 底有啥区别”?
“莫非千年花木专欺生於你”?“莫非新鲜空气比不上浑浊空气”? “你真是怪”。怪?水清则无鱼,我们可是来自於浊水污坑之人,你说这儿环境优美 ,空气清新,鸟语花香,繁花似锦,人间天堂,可我就是要害病,就是呆在污浊之中 而如鱼儿得水,你奈何得了我?
千年花木的芳泽汇入了俗世的嘈杂,并脱掉一层来自荒野远古的气息时,如我 辈浑浊之人恐怕才能消受。而百年的庭院如果失却中国式庭院的拥挤而一派繁花似锦 ,那种历经久远积淀而来的情愫,并只在假山盆景中才能观一花赏一叶,叹它们风姿 绰绝的我,不得“花粉病”才怪呢!花粉病只不过是貌似对环境不能适应的片面极端 的例证,而这仿佛反射出一种文化的积累,又仿佛是一种民族素质的磨砺。但这种积 累与磨砺是否确实能移植与改变呢?如果不能,那麽,漫长岁月里,我们的祖先在惊 涛骇浪里为移民植根异乡而付出的代价,不就组成了一种让人痛心疾首的悲哀?谁能 断言中华文明就一定会在异国他乡开出花朵?谁又能说即便好不容易开出的那几朵有 限的花又会永不凋谢?纵观海外华人的处境,我是绝不看好。印尼华人、马来西亚华 人、美国华人、澳洲华人、纽西兰华人……华人的地位,华人的所作所为,几乎全是 可怜巴巴、腻腻歪歪、苦不尽甜不来的。当然极个别华人神经坚强,自我感觉良好, 有点沾了洋气便以为一览众山小;或以为中华文明能在下个世纪侵袭洋人文明;以为 极个别的洋人尝了个把饺子,娶了个把中国女人,嫁了个把中国男人,就以为种族歧 视已销声匿迹;以为极个别华人的所谓成功,就能代表整个华人融入了主流社会…… 如果这一切真如此,那麽“爱派克”高峰会议江泽民主席亲临纽西兰,此地华人就用 不着欢欣鼓舞,等着镁光灯下拉着江主席的温暖大手而留影;国庆五十周年即将来临 ,也用不着大唱“祖国颂”。如果能融进主流社会,同化到六亲不认,恨不得黑发染 黄、皮肤漂白,还用得着如此这般吗?总之说到底我们就像个常年得着“花粉病”的 患者,无可奈何,流着泪“好辛苦”,可还是硬撑着没有回头路可走。中华弥猴桃酸 涩只有鸡蛋大小而移植到了纽西兰成了KIWI果,就身价百倍地硕大如雅梨而甜甘可口 ,倍受洋人世界亲睐。可海外华人绝没有中华弥猴桃般幸运地能在异国他乡变种成功 。假如一种文明很容易从血液里替换掉,那麽这种文明本身就不成为文明而失却生命力。 在我心中,千年的花木与百年的庭院,最美最惬意最领人神往的,依然在中国 ?
声明:在澳纽网频道上发表的内容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的目的,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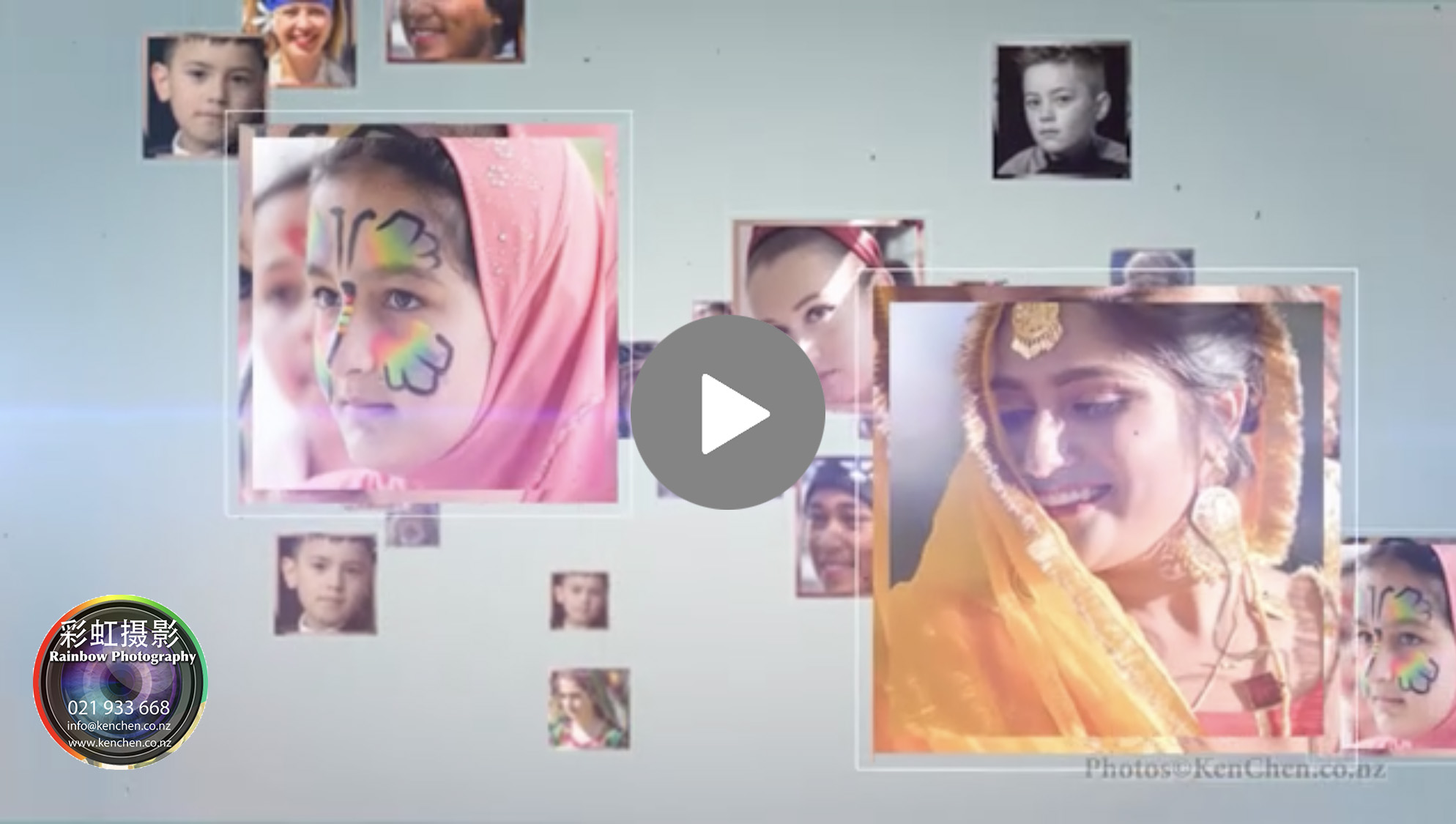


感谢您对澳纽网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