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人物频道 > 心水:充满人道精神的多产作家
作者: 莊偉傑 人气: 日期: 2009/9/14谈论澳洲华文文学,心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重要角色。如果说,澳华文学的形成和发展是凝聚着几代华文作家的热情和心智,那么,有个别重要作家则对澳华文学的历史进程起到承前启后、推波助澜的作用。心水应是其中之一。
心水(1944年— ),原名黄玉液,祖籍福建同安,出生于越南南方湄公河畔的巴川省,属于第二代华裔,他在出生地所办的华文中小学读了九年书,曾经过商、教过书,在工厂当过行政主管。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开始其文学创作生涯,青年时代在越南时就参与海韵文社及风笛诗社的创作活动。著述颇丰的心水,自1978年举家乘船奔向汪洋抵达印尼、次年移居墨尔本后,重拾文学梦,秉笔写春秋,一路耕耘一路播种一路收获,除了出版诗集《温柔》(1992年)、散文集《我用写作驱魔》(1995年)、微型小说集《养蚂蚁的女人》(1998年)和《温柔的春风》(2000年)等外,曾以《沉城惊梦》(1988年)、《怒海惊魂》(1994年)这两部长篇而惊动许多读者的魂魄,并因此而荣获台湾地区海外华文著述奖小说类首奖。在澳华文坛,心水堪称是一位十分活跃的、多产的实力派诗人作家。他写小说、写散文、写现代诗,也写随感杂文式的评论。在一定程度上,他作为小说家的声名超过他的诗名。然而,他对缪斯女神至死而无悔。说他的诗是“温柔的心水”,是因为怒海余生、大难不死的心水,灵魂不死、精神不死,加上历史机遇和个人机缘,生活经历曲折、离奇而丰富,一旦安居于自由而民主的澳洲,诸种因素加上他的智慧和勤勉,驱使他不断律动出心之向往、心之哀怨、心之颤音、心之韵律,仿如行云流水般显得平静、清柔、温润、活泼。
心水给人最深的印象是具有多方面的艺术修养和表现出相当优异的文学才能。一方面是他善于运用多种文体进行写作的能力,另一方面是指他对文学组织团体活动的努力和推行。
心水以创作长篇小说为初具形态期的澳华文学带来一片惊喜。作家依据早年的越南生活、海上漂流以及定居于澳洲后的生活经历为背景,把异域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熔于一炉。其小说作品,较多反映社会生活中的人性问题,故事呈示线性发展脉络,写实性、批判性和强烈的人道精神,使他的小说富有立体感,精炼、平实的文字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尽管其描写不以细腻见长。心水在小说方面的成就,除了后期专注于微篇创作外,最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当属其第二部长篇《怒海惊魂》,显然的比起他初涉澳华文坛时书写的第一部长篇《沉城惊梦》,无论在艺术技巧和视野上都更为开阔、更有力度,也更凝重。如果说“惊梦”仅是向读者提供一场充满灾难性的人生浩劫的纪实性历史备忘录,在艺术上乏善可陈的话,那么,“惊魂”所展示的应是20世纪特定的背景下那些遭遇不幸、离乡背井的难民在海上历险的一波三折的故事,不仅真实地反映了人在大自然风景中颠簸漂泊的求生愿望和强烈的对于自由安宁的向往,而且巧妙地浓缩了个人与社会关系所构成的矛盾。如是,历史真实性、现实悲剧性和文学艺术性便构成为这部长篇小说的特色。关于微篇小说,因文体本身的限制,只能凭藉“以小见大”的方式来架构篇章,表现生活。心水善于选取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或情感片断、或琐事闲情、或社会现象,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人间世相,百态人生。这些与其笔下曲折的故事、丰满的人物及擅长勾勒和传神的技巧是分不开的。如收在《温柔的春风》中的《水灯梦》《望尽凌角》《柔情似水》《夜来幽梦》等篇目。可能与他的诗人气质有关,他笔下的标题很少直接揭示小说的具体内容。他机智地在小说情节的进展中先设置一种悬念来谋篇布局,力求做到故事性强,人物形象鲜明突出。而善于选材和时常采用一些富有生活气息的口语,拉近了读者与作品之间的距离,也吸引了许多读者的思维。
心水的诗歌以抒情见长,他在继承传统文化中深受中国古典诗词的滋养,又领略到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潮的感染,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台湾现代主义诗歌的艺术手法和表现方式。心水的诗也有唯美倾向,这集中体现在他对诗的语言和处理上。他喜欢让传统(古典)的文化踪迹与现代的生活思维、语言语境在传承的定式中呈现在诗歌文本里,使古老的文化语言在现代生活中继续保持充沛的生命力,这种坐怀不乱、处事不惊且始终维系着的那份古典诗歌情怀,使母语尽可能在描述中达到较高的艺术审美层次。他对语言的这种处理,既重视汉语特征的内涵与外延,又能在交流中自然地走进读者的心灵,使诗歌文本和诗人的心境与读者的理解方位和趋势,能够自然地产生认领和契合。譬如,《悉尼谊园》《蝉声》《三月骚动》《烟花》《树之死》等诗皆然。在《如是我闻》一诗中,诗人这样表达着——
把桂林那片灵秀的山水
小心翼翼的折叠起来
放进手袋,然后将漓江
挂在口里诱惑我
说到台北,凌乱令你心悸
台湾同胞用暴发户的嘴脸
闹着要独立?原本美丽之岛
居然阵风阵雨
香港街头竟已都是
一些九七的忧容
盈耳是移民话题
红旗未升,东方之珠铅笔渐落
从你沾满灵气的笑意中
我掇拾了海峡三地
零碎的点滴。唉!除了风景
甲天下,除了风景?唉!
这首诗的意象是立体的、跳跃的,口语化的叙述中让人走进风景之中,并在辨明风景之后叹息。由于诗人对故国山河满怀向往之情,然而现实中却由仰慕、钟情直至深感惊愕和疑虑,最后竟演绎成无尽的叹息。而诗以“如是我闻”的佛经用语做“诗题”,别具匠心,诗题与诗文的两相配合,使诗的忧思、爱意产生一种缠绵的、连锁的效应。结尾那一声“唉”叹,仿佛发自心底来自灵魂深处,令人感同身受。
由于具备驾驶小说的创作功力,又具有诗人的禀赋才情,散文写作在心水笔下就显得从容而自如了。小说重叙事精于结构安排,传统诗歌重感觉讲究意境词采。如能将两者加以结合,那么这样的散文不仅既有诗性品质,更为散文提供了广阔的表达空间。心水散文显然在方面作出相当的努力,而且洋溢着生活情趣和充满着人生感悟。他以《我用写作驱魔》作为自己散文集的书名,“实际上强调的乃是文学创作在抚慰自我心灵、调节内心情感方面所具有的巨大功能,其意义既是审美的,也是心理的。” (1)他的散文如《一枝草一点露》《跌进乡音里》《野猫风波》等篇什,或抒写亲情爱恋,或怀念家园故国,或状写日常琐事,显得亲切而自然。
由于文化、地理的等因素使然,尤其是时空的隔离,国内读者很难读到或掌握到海外作家创作的文本,特别是像心水这样生于越南而后移民于澳洲的第二代华人作家。况且,海外作家个人的生命经历、体验、感受,如同弯曲的空间,如有南十字星空下闪烁的灯盏,其折射的关于自身生命的存在方向和价值坐标,更难以为国内更多的读者所了解。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或者经济、文化的发展的不平衡性,尽管所处的是一个倡导多元文化的国度,但毕竟是身处边缘,因而文学写作就自然的呈现出另一种情状。无论从哪个方面观看,这些华文作家都像是时间上的移民,处于人们所熟悉的环境之外,或者说被置放于被人忽略的角落。诚然,像心水这样多面手的作家毕竟为数不多,我们也发现其作品中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譬如题材重复的现象、手法缺乏灵活多变,观念先行或思维定势的形成等等。然而,生活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价值取向、思维观念和生存空间等毕竟不尽相同,由是,理解和评价作家的标准可能也难以对等。对此,许多问题有待于我们作更深入更全面更立体的思考。心水作为一个在海外成长的诗人作家,其过人之处显而易见,其不足之处同样存在。或许,他属于另一个世界,他不是“中国式”的作家,而是一位既有传统格调又有现代意识的海外华人作家,一位充满着人道精神的华语书写者。

心水 攝於雲南
(按:本文作者現為廈門國立華僑大學華文學院教授)
注释:
(1)参见陈贤茂主编:《海外华文文学史》第三卷,第七章(第二节心水、徐家祯),厦门:鹭江出版社1999年版,第457页。
(原载《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42至345页)
声明:在澳纽网频道上发表的内容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的目的,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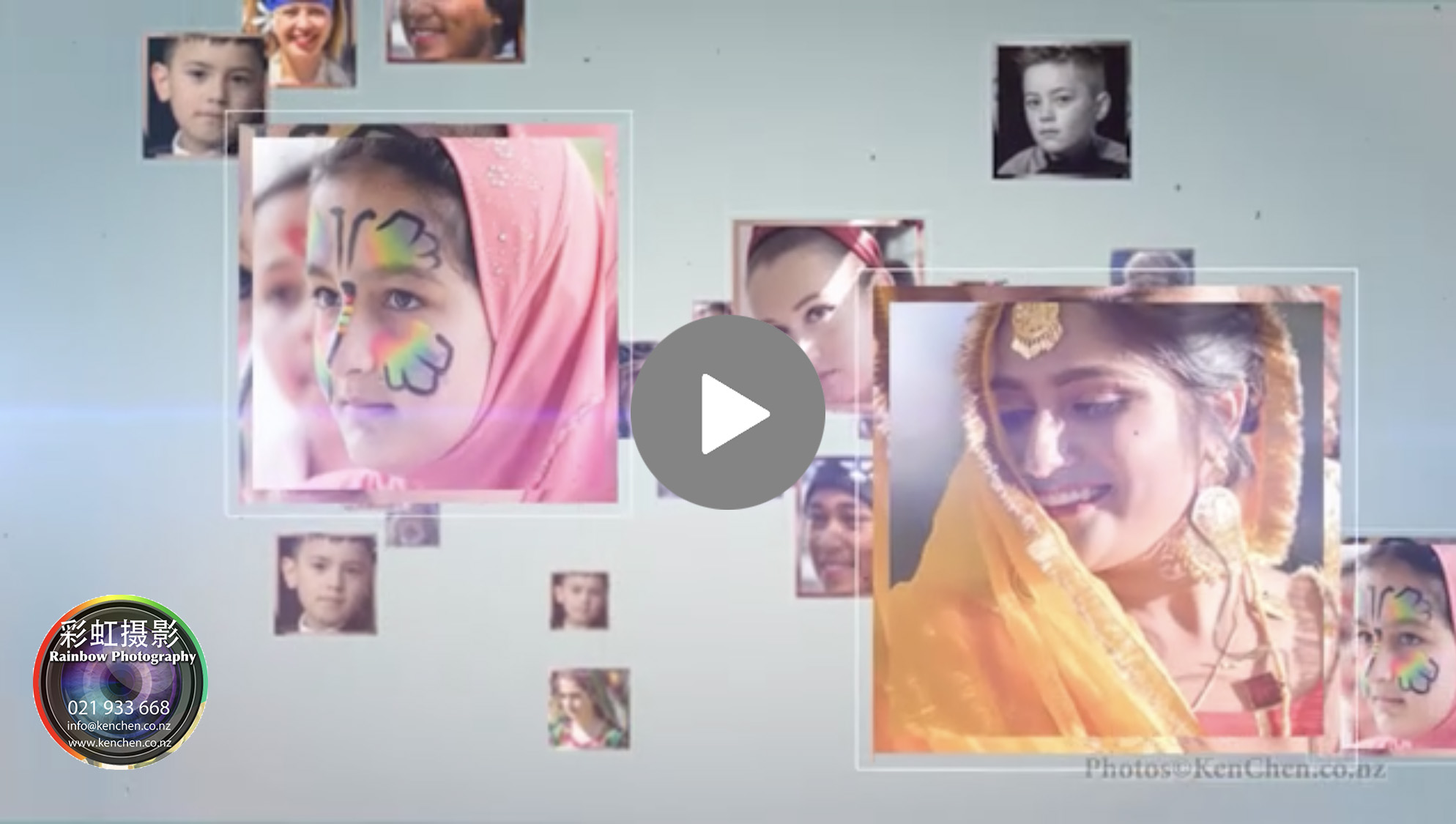


感谢您对澳纽网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