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新西兰旅游 > 激流岛游记
作者: 午夜太阳 人气: 日期: 2005/7/30 但凡写诗的国人心目中有两个圣地,一个自然是徐志摩流连忘返的康桥,另一个就是顾城上吊的那个激流岛了。顾城当然比徐志摩更让人亲近些,毕竟是离我们不太远的人和事,因此激流岛就自然比康桥更让我有感觉。因缘际会,我终于可以亲赴这一场期待已久的心灵约会,去凭悼一下这位朦胧派的鼻祖。
其实我并不喜欢顾城的诗,当然也不喜欢舒婷的,他那个时代的诗人我只勉强喜欢北岛,因为那个时候我只喜欢我自己的诗。因此我去激流岛的目的与其说是凭吊顾城,倒不如说是去凭吊谢烨,那个死在了自己丈夫斧下的美丽女人,那个有着无比才情却一生错爱的女人中的女人。我至今仍想不明白她当时是爱上了顾的诗还是爱上了那张小白脸,不过不能否认的是在当时写诗的人中顾的确长着一张还算端正的脸。
事实上激流岛这个名字在当地除了华人(特指大陆地区的华人)基本上没人知道,这个岛的英文名字叫WAIHEKE,看发音象个毛利语,离AUCKLAND只有三十分钟船程。激流岛这个名字的由来大抵是因为《英儿》的缘故。很多初来咋到的人急急忙忙打听的不是邮局警察局公车站在哪里,而是问谁知道激流岛在哪里怎么去,接着再问谁知道顾城上吊的那棵树在哪里吗?所以当我说要去激流岛的时候当地的朋友一脸意料之中的神情。
站在开往激流岛的渡轮的甲板上,看着船体犁出的海浪,听朋友介绍着岛上的情况。原来当初顾城定居小岛的时候岛上只有他们夫妇和顾乡三个华人,房价也相当低,远没有近几年因为大批富人移居和大量度假屋的建造而导致的价格暴涨。现在的小岛已经是一个富人区了。在我们的渡轮所经之处可见海面上散落着许多游艇和帆船,有的在钓鱼,有的在晒太阳,有的则在玩着各种水上运动。朋友说在这里游艇其实是很平民化的玩意儿,一般工薪阶层都玩得起。听到这我不禁在心里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句:“草!”但我想顾城当初选在岛上住肯定不仅仅是房价低的理由,虽然我读过的一些怀念顾城的文章里都有提到他当时非常窘迫,但当时在市区里稍偏一点的房子也不贵。他或许更多的是想寻找一个梦中的天堂,一个远离繁嚣的世外桃源吧。
这时候站在我们身旁不远处一直在和一老外拥吻的华人女子也许是偷听到我们字正腔圆的国语忍不住搭讪:“我们正去的这个岛真的就是激流岛吗?”我看看她那件几乎把两个大奶都露在了海风里的小背心撇了撇嘴,心想废话你不打听清楚了怎么会勾搭这洋老头上船来?还是朋友已经完全西化了,极有绅士风度地告诉她说是的错不了。我正想埋怨他怎么会理睬这辱没国体的女人时,又听到他非常小资地喊开了:“看,那就是激流岛!”
看着渡轮慢慢驶过一片游艇停泊区靠向码头,我的心忽然一阵莫名的加速。不能完全说是一种激动,那是一种和期待已久的恋人初次见面才会有的心跳,却又有点近乡情怯的犹豫。坐在出租车上和那个典型的雅利安大脸上还留着尼罗河上的惨案里的侦探波洛的八角胡子(可有日子没见过这种胡子了)的司机闲聊,他告诉我们说这个岛有新加坡那么大。我很惊讶于他的比喻及机敏,事实上后来我知道这个岛的确比新加坡还大。
他还告诉我们他就住在岛上的海边的一幢HOUSE里,于是我们恭惟说啊您真有钱啊是富人哦,结果此君居然在那张南极臭氧层空洞强紫外线照射下腥红点点的大脸上更增添了几许红晕,谦虚地自嘲说富什么啊就是一开出租的挣不了几个钱。因为聊得愉快所以在下车时吩咐不必找零,于是又挣来胡子司机一连串的感谢好象得了我们多大恩惠似的,完全没有北美地区出租司机那种拿了还闲少的嘴脸,足见本地民风之淳朴,让我们感叹不已。
站在岛中心镇的主街上,我们有点茫然四顾。朋友问我们要去找顾乡吗她该还在岛上,据说还开着一家店的。我很有些犹豫,自己也不确定是否要去那个凶案现场,也怕自己的耳边会传来那被自己最爱的人砍杀时撕心裂肺的哭叫声,更不愿意在那棵上吊的树下留影啊什么的。思量再三最后我还是说算了去了又能怎样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再说我真怕自己到了会抑制不住的悲痛。朋友睁大了那双绿豆眼夸张地说不会吧至于吗你A型血处女座啊?
我翻了翻白眼然后把目光定格在远处的蓝天白云下并刻意失去焦点后再用情人呢喃般的语调说其实我的梦中情人就是谢烨那款默默为丈夫打点好一切并在出差行李中备好避孕套的女人,这么好的女人被他娶了去还被他杀了,我能高兴得起来吗?朋友笑骂是是你还恨不得还能有一个英子性欲强烈能长伴左右可随时享用。我正色道我鄙视英子比鄙视木子美更甚。最后我们讨论的结果是放弃顾城而去岛上的一个著名的天体海滩晒太阳。这个提议让我满心欢喜,脚步也紧了许多,仿佛赶着入洞房的新郎。
在路上我又虚心好学地打听着关于天体海滩观光是否也得把衣服脱光之类的礼仪问题,朋友哈哈大笑说没那回事别老冒了在国内的人都瞎传,其实这里的人敢脱光了就压根不在乎人看,当然你要想死盯着人大姑娘的奶子看的话那就最好把墨镜戴上更不好拍照的。我说那就好那就好以前在别处我就老是因为没有施瓦辛格的身材没敢去瞧,这回得把这空白填补了。说话就到了,放眼望去,海滩上人很多,穿着布极少的三点式爬着晒太阳的MM也不少,但老人孩子更多,就是没找着一个不穿的。
正扭头想发泄上当受骗的不满时朋友说别急啊接着往里走。原来这个海滩分两块,这边是公众游乐区,天体区还得顺着海滩往里走,不远处有几个大礁石拦开了另一个天堂。在绕过礁石的时候我一把扯住了朋友紧张和踌躇地问就这么进去了?朋友又笑怎么还得化状啊瞧你那点出息。于是我深吸了口气并压了压头上的帽沿同时耳畔响起了国歌的旋律。
一绕出礁石就吓了我一跳,眼前就正站着两个全身上下一丁点儿布都没有的大姑娘,看样子是刚从水里上来,正拿着浴巾擦头发呢。两只饱满而坚挺的乳房骄傲地炫耀着青春的活力。因为太近的缘故我几乎楞住了,看来国歌也不怎么管用。
我们选了个离岸有点远的树荫下坐了下来,正好可以环视整个沙滩而不被人注意。这时候朋友开始脱鞋子和衣服边脱还边劝戒着我说入乡随俗入乡随俗。我有些不情愿但还是也象他一样脱光了躺着,假装晒着太阳眼却藏在墨镜后四处如饥似渴地看着。在我们不远处有一对情侣,男的仰躺着似乎很享受紫外线对他肌肤的伤害,女的拿着一本书看得很入迷但有一只手却在那男人的大腿上游走,估计看的也不是什么好书。胸型有点下垂显示出纵欲过度的征兆,但依然不失长年吃三成熟牛排孕育出来的茁壮。在远处的海上停泊着一艘游艇正是我喜爱的那一款型,洁白的船体在明媚的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甲板上有几个裸体的青年男女在嘻闹。在离岸边不远的海水里也有三三两两的男女在欢笑着玩着潮,跳跃的身躯在阳光下真象古希腊传说中刚从海里冒出来的精灵。
天空和海水都是醉人的蓝,在地平线的尽头混然一色。雪花般的海浪轻轻地不断拥吻着沙滩再幽幽地退去,和煦的海风微微地拂过我赤裸的身躯,让人产生一种庸懒的惬意,我甚至都怀疑自己可能天生就是一个裸体主义者了。我歪着头自言自语般问朋友你说顾城他们仨会不会也来过这儿晒过太阳?肯定来过但不知道是不是仨一起来的,是中国人都会来。朋友望着远处并没有回头看我。于是我的脑海里开始设想顾城到底是和老婆来的呢还是和情人来的,或者是一起来的,来了后他们会干些啥等等一系列在怡人的树荫下品茶时通常都会做的胡思乱想,并俨然打起了另一部情色巨著的腹稿。可我的主脉络构造还没有完成就见朋友忽然翻身坐起冲着我说走我们到水里泡泡去顺便和那几个妞套套瓷不定晚上有篝火狂欢呢。我发出了一个鼻音然后说要去你去我还是离那些妞远点好免得有尴尬情形出现出丑得紧。朋友不由分说来拉我得啦吧要真那样我保证如狼似虎的不是你。我只好站起来嘴里却坚持着得得你甭拽人还以为咱是同志呢。朋友已然向那群精灵冲去了,我却慢吞吞地边走边琢磨着到自我介绍的时候我一定得说自己叫亚当。
事实上我设想的一切都没有发生,那群美丽的精灵显然并没有把我俩当回事儿,一阵礼貌的哈楼和嗨之后就再无下文。我看着朋友有点下不来台的脸赶紧解嘲说不定真把咱俩当同志了。朋友有些讪讪笑容里也有些苦涩说草这儿同性恋和妓女都TMD合法。于是我们怏怏地草草结束了这次回归之旅,决定在天黑以前赶回CITY 晚饭。
重站在渡轮的甲板上望着渐渐远去的海岛,我点燃了一根香烟漠然不语。忽然想到不知顾城的儿子现在怎样了,算来也该是个挺拔的大小伙子了。不知道成年后的这个有着可怜身世的孤儿是怎样看待自己的父母的呢?他是否健康快乐?是否对这个世界还有信心?是否还能够坚强的面对今后那漫长的人生路呢?想到这里不禁黯然,狠狠地从胸腔里喷出一口尼古丁对着已经模糊的海岛狠狠地说:人生,有些时候必须学会忘却。
声明:在澳纽网频道上发表的内容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的目的,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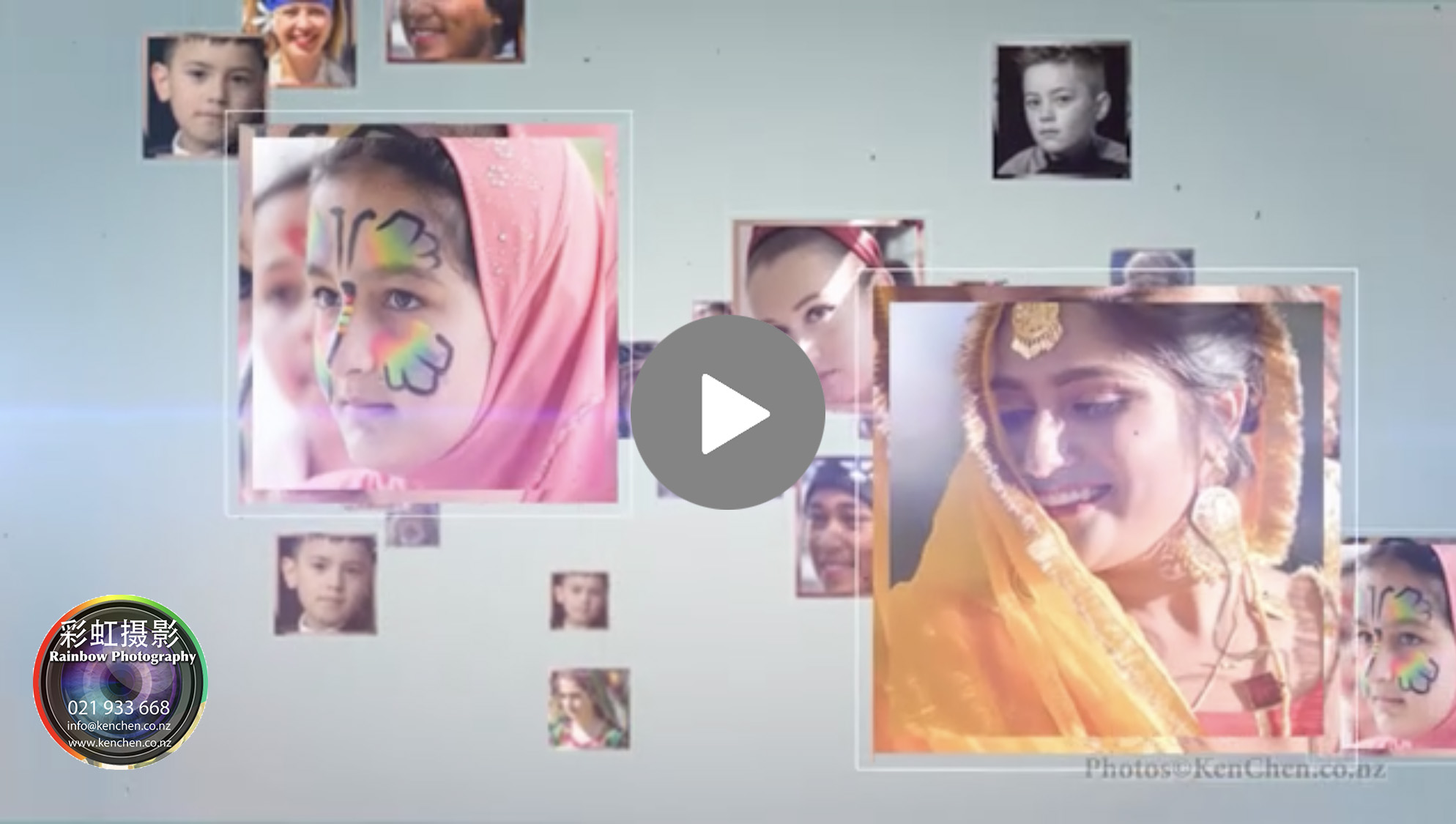


感谢您对澳纽网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