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读者文摘 > 让人为难的罗素
作者: 朱学勤 人气: 日期: 2004/6/4大陆中青年学界在反思五四思潮。这样的反思有积极意义,只恨相见太晚。反思中,也有这样一种观点在流行:五四中西思想交汇,保守主义者与激进主义者分别师承英、法,从法国过来的激进宣传受激进主义者青睐,从英国过来的保守学理则受保守主义者欢迎。依此推理,自然就鄙薄法国,崇尚英国,似乎英国知识分子都是保守型君子,法国人多为轻浮的激进分子。五年前,我自己也是这样一种观点,并试图以这样一种认识重新梳理法国左翼传统对中国近代观念史的影响。我将这一源流称为“法国病”:好言革命,动辄起义,中国近代意识形态的血液里即有这一成分,至今尚未淘洗。
如此二分法一开始亦无大错。但是一旦流行,而流行往往反而意味着凝固,凝固为一种流动着的僵硬模式,事情则会走向反面:就史实层面而言,可能削足适履,简化甚至歪曲五四中西思潮交汇时那些错综纠葛的历史事实;就现实层面而言,或许会以反思五四激进思潮为学理托辞,抢先责难并抛弃知识分子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而真正应该淘洗的那些思想观念却遮盖起来,不去批判。这样,一场健康的反思还未走完正途,即有可能从反思走向绥靖,中途变质,变质为一种曲学阿世的时尚。事实上,一种过分的倾向已经发生,某些观点嫌否定五四还不够,要一直否定到辛亥,甚至否定到戊戌,即为显例。我私心以为,保守主义的精髓,是求社会发展、文化建设与人格发育的平衡,而不是偏向另一个极端。在扬弃法国式革命狂热的同时,是否应该把知识分子理应担当的社会责任从那张皮上小心剥离下来,“保”而“守”之,这才是一种健康的保守主义态度?然而新出的危险却是,不倒脏水倒孩子,脏水还在荡漾,孩子却可能已经扔了。
最近读到一本中国人写的《罗素与中国――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一次经历》,或许有助于思考这一问题。
伯特兰.罗素的名字,对今天的大陆读书人来说,已经耳熟能详。这个人的一生,令很多人羡慕,不仅仅因为他寿命长,情人多,更重要的是,在学术成就与社会责任两方面,罗素都未偏废,而且达到了两个高峰。读罗素的学术著作,冰清玉洁,如不食人间烟火;读罗素的时评政论,则道义滂湃,每当社会发生重大事件,都能听到罗素不畏权势的激越抗议。几乎难以设想,罗素这样的纯粹学者竟也会因为不同意见,两次入狱,最后一次是一九六一年,当时已达九十高龄。百年人生,他始终将知识关怀与社会关怀这两个似乎水火不容的极端,相融于一身,肯定很不容易。但是有罗素这一成例,也许有助于说明,“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个知识分子可以坚持至少可以向往的境界。
可惜,一九二○年罗素应梁启超等邀请,来华讲学,没有取得相应成功。相比他的辉煌一生,这是一次令人遗憾的思想旅行。当时,正是中国五四运动的第二年。炎黄青年如火如荼,翘首以待,可以想象。无论是激进、保守,对他都是满怀期望。结果罗素不激不慢,不温不火,既劝中国人走国家社会主义道路,又对正在试验这一模式的布尔什维克持严肃批评,使得当时的中国人大惑不解,始而期望,继而失望,最后是讥评四起。在华讲学期未满,主客双方都觉得尴尬起来,以至罗素后来是带着遗憾,带着不满,离开了中国。
先说两国政府的态度。
英国当局因为罗素在一次大战期间参加反战运动被监禁过半年,对他始终心怀猜忌。一九二○年十月十二日,罗素在上海上岸,中国学界的接待人员尚未赶来码头,英国驻华使馆与伦敦的外交部、国防部即已函电交驰,设想乘其立足未稳,干脆撵回英国。以后罗素在沪、宁、杭、京讲学十个月,始终处在英国情报机构的“内控”监视之下。北洋政府方面,一九二一年三月间,因其在华宣传“危险思想”,也曾考虑过要将罗素驱逐出境。所谓罗素的“危险思想”,可能是指一篇被上海共产党组织印为传单的《共产主义理想》。但是,《共产主义理想》主要是从理论上阐释共产主义合乎人类理性,并没有直接号召中国人从事共产主义运动。北洋政府几次犹豫;最终没有下手。被当局如此猜忌,而且还提供危险的“小册子”,按中国人的逻辑,是该受到在野一方激进党人的欢迎了。比如说当时的“南陈北李”?
按照《罗素与中国》一书所叙述的罗素在华日程表,李大钊与罗素似乎没有接触。从陈独秀的态度推测,李对罗素可能是敬而远之。陈独秀参加过北京七团体欢迎会,以后听罗素讲演,越听越觉得不对劲,熬不住,给罗素写过一封信,请教疑难:“近来中国有些资本家的政党的机关报屡次称赞你主张中国第一宜讲教育,第二宜讲开发实业,不必提倡‘社会主义’,我们不知道这话真是你讲的,还是别人弄错了呢?我想这件事关系中国改造之方针,很重要,倘是别人弄错了,你最好是声明一下,免得贻误中国人,并免得进步的中国人对你失望。”(《陈独秀致罗素先生底信》,《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据称,罗素曾给陈独秀写过复信,可惜中途遗失了。不过,按罗素当时的思想状况以及陈独秀没有下文,这封信不太可能使陈独秀满意。
这时,《新青年》编辑部分裂,“问题”与“主义”之争已经爆发。罗素来自英国,具有鲜明的逻辑实证主义经验论色彩,胡适导师杜威亦推崇罗素是世界三大哲学家之一,比他自己还高明;罗素显然不会简单赞同“主义”派,而且确也引起了“主义”派的不满;这些情况都该说明罗素理应得到“问题”派的青睐。结果也奇怪,胡适对罗素访华十分冷淡,并不热情。当时赵元任准备应聘为罗素作翻译,胡适即警告赵不要上梁启超“进步党”的当,力阻他为罗素效力。以后,始终也不见罗素与胡适交往的记载。
那么,对罗素热情最高的是谁呢?可能是当时难以归入某一派别的张东荪。然而,张东荪期望最高,失望也最深。当年张东荪三十出头,身任《时事新报》和《改造》杂志主编,又兼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主任。他是通过阅读罗素的《自由之路》等著作成为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罗素来华之初,张东荪表示对他“崇拜到了十二分”,他还建议罗素“实地去研究中国的同业公会,因为欧洲中世纪之基尔特已经无存了,不能不在中国寻其遗迹,从此遗迹上或有些贡献也未可知。”
意外的是,罗素在中国时间越久,与他的思想距离便拉得越大,最后竟至于建议中国仿效苏俄,走“国家社会主义”的道路。罗素离华半个月后,张东荪终于发表了一篇《后言》,抱怨罗素“自己的思想还未确定,如何能知道我们呢?”张东荪奚落罗素是说“梦话”,并断言罗素“对于中国情形毫无所得”。
毛泽东的态度也有点意思。罗素在长沙讲演《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润之先生当时在场。有些史籍还说罗素讲演时,他担任过那次会议的秘书,不可谓不热情,题目也非常配他的胃口。但是听完讲演,毛泽东给遥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友人写信,冷冷说道:“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毛泽东致蔡和森信,一九二0年十二月,《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页)大概是因为罗素在这次讲演中,虽然为布尔什维克的经济模式辩护,却尖锐批评了布尔什维克政治体制。
北大师生自发组成了一个“罗素学说研究会”。罗素在华的主要时间后来就是在这里传业释道,每周参加一次他们的英文讨论会,每两周参加一次他们的中文讨论会。一位自称已经研究“哲学”多年的成员,在参加了该研究会第一次讨论会后,便写信给赵元任抱怨:“我发现他的研究班仅仅局限于技术哲学,这使我很失望。现在我冒昧要求不再参加以后的讨论会。这并不是因为我对那些问题望而生畏,而是因为我对技术哲学几乎毫无根底,也几乎毫无兴趣。”(Coken
Chen致赵元任,一九二○年十二月十日,原件存罗素档案馆) 感觉苦恼的不仅是中国学界。献花、掌声过后不久,罗素自己的感觉也逐渐败坏。从来华第三个月、赴京第二个月起,罗素即开始有怨声:“当一切都变成了例行公事,中国的欢乐便消失了。”(一九二一年一月三十一日,罗素致柯莉)他感到,与北京的学生们在一起,对他本人的哲学进展毫无帮助,因为中国学生的基础知识太差,真正能领会罗素纯哲学的中国人其实很少,与他们讨论高深的哲学实际上是徒劳无功。罗素原是应邀到中国来讲述哲学课程的,但他刚来中国就发现中国的主顾们兴趣不在这里,“他们不要技术哲学,他们要的是关于社会改造的实际建议。”(罗素致柯莉,一九二○年十月十八日,原件存罗素档案馆)罗素断言,“中国非常压抑,它正在朽败腐烂,就像晚期的罗马帝国一样。”(同上,一九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对于那个名盛一时的“罗素哲学研究会”,罗素后来也不无揶榆,说他们“除一位逊位皇帝的侄子外,全都是布尔什维克分子”。他个人对布尔什维克分子抱有西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特有的同情,当时还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帮助过中国学生进入苏俄。(Chen
Ting-Fan致罗素,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此信对罗素的帮助表示感谢,原件藏罗素档案馆)从他的小册子《共产主义理想》曾被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人当做传单印发,甚至可以推测他已知悉中国共产党当时在上海的创建活动(见《先锋日报》(Dairy
Herald)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九日)。但罗素的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信念使得他最多同情这些新的政治势力,不可能直接主张中国人组成像苏俄那种党纪严厉的政党并诉诸武力。至于北京学者群中的社会主义,罗素观感更为不佳。一九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致柯莉信中,罗素写道,中国的社会主义者“两手抱胸,高谈阔论社会主义,而日本人、俄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则都忙于掠夺中国的富源”。 使人气馁的是,罗素甚至还透露出当时在华的杜威表面上不说,骨子里也有同样的失望:“中国人没有心肠、懒惰、不诚实。他们将赈灾事务全部推给欧洲人,而且他们的政府极端腐败。绝大多数学生愚蠢而又胆小。我并不真地认为我在此间所做的一切有什么价值。杜威夫妇在此呆了一年,他们已完全失望。”(罗素致柯莉,一九二○年十二月三日,原件存罗素档案馆) 这场“西方思想在中国的经历”,实际上是在还没有结束时就已经结束了。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可能得从罗素在华讲演的总体内容去寻找。罗素在华发表的哲学主张以五大讲演著称:《哲学问题》、《心之分析》、《物的分析》、《数学逻辑》和《社会结构学》。此外,为满足中国人当时对社会政治思想的渴望,他有过两场关于布尔什维主义的讲演:《布尔塞维克与世界政治》、《布尔塞维克底思想》。告别中国时,发表具有临别演说性质的《中国到自由之路》。综合这些言论,他的总体特点是: 第一,在哲学方面,神秘臆想被拒之门外,只有具备较高的自然科学素养才能登堂入室。罗素是由数学入哲学,而不是由文学入哲学,他所认可的哲学是建立在自然科学最新经验的基础上,与玄思冥想无缘。他拒绝黑格尔式的欧陆哲学,开辟了数理逻辑实证主义。对于听众而言,连杜威也承认:“有人说,世界上真能够懂得数学的哲学的人,至多不超过二十人,我既不是二十人之一,我也不能懂得。”(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第二,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既同情苏俄革命者的社会主义理想,亦批评苏维埃政治体制的压迫性弊端。罗素来华前曾经专程访问苏俄,对苏俄模式有褒有贬。让中国听众困惑的是,他不认为苏俄的弊端是出于对西方主流文化的反叛,相反,他认为苏俄的弊端――政治权力的高度垄断――是西方财产寡头体制的翻版。他是最早向中国建议采纳俄国人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人,然而,也是最早提醒中国防止俄国政治弊端的人。这样的观点反映了一次大战后西方优秀思想家对社会主义理想的普遍向往,同时亦保留了英美自由主义传统的可贵底色。这与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大幅摇摆,要么是西化,要么是拒斥西化的俄化,有一段很大距离。 第三,他强调知识分子的实践精神,厌恶中国人的坐而论道。他在梁启超、丁文江给他举行的饯行宴席上说,中国要有“一打好人”(GOOD
MEN),敢于承担责任,敢于将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临别演说《中国到自由之路》对中国人提出十几条建议,最后一条是把那“一打好人”扩大为“一万名果敢坚毅之士(RESOLUTE
MEM)”。然而,这样的“一打好人”、“一万名果敢坚毅之士”,肯定不是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家,而是像罗素在英国参加的费边社式那样的知识分子,有自由主义理念,又能脚踏实地,坚韧渐进。 不难想象,中国听众面对这样的讲演,会出现什么样的面部表情。尽管听讲人数不会太少,但是内心的疑惑与误解则难以掩饰。中国的知识传统以文学性文人型著称,而不是以科学性学者型见长。它能哺育出大批文人,乃至过剩,却难培养出在质量与数量上合格够用的学者。由此养成的中国知识传统,实际上只成就了一个文人传统,而不是学者传统,至少前者要比后者强大。每当思想激荡的年代,涌进哲学大门的多是文学青年,至今还是如此。要无数文学青年像罗素那样以冰冷的数理逻辑来思考纯粹哲学,建立纯粹的知识关怀,而且还要拒绝与文学化思维特征天然接壤的欧陆思辨哲学,就“事”论“事”,不能玄思冥想,真比杀了他们还要难受。即使在今天,大陆知识界也还是如此,未必能达到罗素的要求。此其一; 其二,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他固守英国哲学传统中源远流长的怀疑精神,同时亦不缺乏法国人文传统中的热血担当。他号召中国人迅速发展工业大生产,同时又劝中国人警惕社会有机化对个人自由的侵害;他建议中国人效法苏俄走“国家社会主义”的捷径,同时又指出“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并不美妙而且病弊丛生;他鼓动中国人迅速培养起爱国热情,同时又要求中国人必须将爱国热情严格控制在适足以救国的高度;他赞成中国人从事社会政治运动,但又要求中国人保持平和沉静的心态;他希望“少年中国”中间产生成千上万“果敢坚毅之士”,但又避而不谈他们是否应该组成纪律严明的政党。 这样一种社会政治思想,如果一定要放在英美模式与欧陆模式的对立背景中考察,可以说它既非英国的保守主义,又非法国的激进主义,实际上剔除其各自负面因素,综合了两种知识传统的正面因素。对于当时习惯于非此即彼的中国人来说,这样综合性的思想主张,实在是难以把握。 其三,论实践履行,罗素与中国人面对黑暗专制的传统态度也有距离。中国人的习惯:不是去造反,就是受招安,要么揭杆而起,要么缩头作犬儒,独缺当中那种既不制造革命又不接受招安,耐心对峙,长期渐进的坚韧精神。作为费边社成员,罗素赞成的实践方式是:每天前进一寸,不躁不馁,既不狂冒进,亦不受招安;面对不良政治,纵使十年不“将”军,却无一日不拱“卒”。要中国人接受这种费边式的耐心、沉着、坚韧,非几代人的磨砺,难以实现。 罗素可能不知道,这些一时无实用价值的思想,对中国人早说了八十年。就中国人的思想长程需要而言,罗素这些西方思想,倒像中国人所说的“中药”,治本不治标,就中国人当时的短程需要而言,反而是一副陌生而又遥远的“西药”,远水解不了近渴。一直到现在,大陆知识界也未必具备这样的平衡能力,在知识关怀与社会关怀两个方面,能够兼行并举,于此同时,在道义承担与渐进实践之间,又能保持必要的张力。相反的情况倒时常看见:社会情绪高涨时,纷纷放弃知识关怀与渐进实践――见好就上;社会情绪一旦低落,或者仅仅是暂时转移,则纷纷躲避甚至责难社会关怀与道义承担――见坏就收。能够克服这种陋习,在上述两个层面上始终保持平衡,培养一种真正英格兰作风――见好就收,见坏就上,而不是相反,当然殊非所易。然而,这又是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衡量知识界是否成熟的标志之一。 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罗素给英国情人的信中说:“患病之前我就已讨厌中国的北方了,这里很干燥,而且人也冷酷无情。我深感疲惫,归心似箭。”(罗素致奥托林)不难想象,罗素在华十月,表面虽然热闹,内里知音难遇,甚至连象样的对手亦难寻觅。其实他是半年不到,即萌去意,后来因病拖延五月,亦如置身沙漠,只盼早归。拖到七月,能够策杖而行,终于告别中国学界,与杜威同日离京。 罗素怏怏而归,心情不会愉快。离开之后,中国知识界亦觉尴尬,对他的影响力大小发生过一些争论。由梁秋水当社长而雇佣外国人JOSEFW.HALL当主编的英文报纸《北京导报》,于一九二一年八月四日发表了一篇社论,说罗素的思想并未为中国的青年所欢迎,罗素对中国并未产生深远的影响。丁文江在该文发表的第二天即致信《北京导报》编辑部,要求他们撤回这篇评论。丁文江指出,罗素在哲学和社会思想方面必将在中国造成既深且远的影响,正是罗素使中国人第一次认识到哲学应该是对所有科学进行综合的结果,社会改造必须以丰富的知识和深思熟虑为前提。“罗素学说研究会”的成立、罗素演讲录的广泛刊载和流传、罗素患病所引起的普遍忧虑、罗素发表告别演说时听众的拥挤程度,都表明罗素深深地打动了中国人的心灵。(丁文江致《北京导报》编辑部,一九二一年八月五日,原件存罗素档案馆) 平心而论,丁文江过高估计了罗素在华影响。这位在英国受过良好训练的科学家可能是按着他自己对罗素的深入理解,来理解中国听众的理解能力了。 不妨承认,罗素的中国之行是以两方面的失望结束,而中国人的失望甚于罗素,是一种双重失望。 七十年前的中国人感到失望,是因为罗素没有提供一个一面倒的意识形态,不解渴;七十年后的中国人忙于以激进与保守的二分模式切割五四思潮,同样会感到失望。因为无法把他捺入一个要么激进要么保守的简单模子里,甚至会感到恼火。怎么会有这么一个思想家呢?既激进,又保守,或者说既非激进,亦非保守,说他是个激进的保守主义者好,还是个保守的激进主义者好?既有英国人的冷静,又有法国人的热血,或者说是既非英国,又非法国,他是个英国式的法国人呢,还是个法国式的英国人?既然有激进色彩,为何受中国的激进主义者冷遇?既然有保守主义倾向,为何又得不到中国保守主义者欢迎?太让人别扭了。总之,四不像,无论用什么模式都套不进去,让你左右为难,过去为难,现在继续为难,让一切简化模式为难,这才是罗素,这才是真正思想家、真正思想史事件的应有内含。可以说,一部思想史,就是由一系列为难人物、为难事件组成的。罗素中国之行,也许并不成功,但是这场不成功的思想旅行及其主客两方的错综反映,却对那种有关英法知识分子传统、有关五四时期中西思潮交汇的简单化模式,构成了一个有趣的挑战。它促使人们重回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贴着地面运行,怀疑那种非此即彼的二分法;问题一旦想得复杂,那种不是激进就是保守的僵硬模式就会松动;某些似是而非的虚假学理――比如说以批评五四激进主义为名,张冠李戴,暗行绥靖思潮的时髦观点,也就多少露出一点破绽了。有这样一条积极意义,罗素一九二○年的中国之行,不也留下了一些可取之处吗? 是不是罗素太特殊,不能代表英国思想家保守主义的集体性格呢?也未必。英国哲学家柏克的名字现在是京沪知识界较多引用的一个热点。就我所知的有关柏克那一点史料,我觉得大陆知识界对柏克的热衷,似乎也不全面。人们感兴趣的是柏克抨击法国大革命的那篇在英国议会上的讲演,但是忽视了柏克曾经热情支持过美国革命反叛英格兰本邦,而且与十八世纪最激进的流浪革命家潘恩一度是莫逆之交,当国人皆曰可杀时,柏克就为潘恩提供过自己的庄园,衣食住行,好生款待。英国知识分子未必都像中国知识界在今天所想象的那样冷血,连柏克都有另外一面。保守主义者多半出身贵族,在政治风浪中,且不论政见离合,对待落难对手,起码具备骑士侠义的一面。离开这一点而奢谈保守主义,只会让这些昔日贵族讥笑为小郡市民的假冒伪劣。当然,真正能够避免法国知识分子的革命狂热,同时又能凸现知识分子社会良知的典型,确实不是古典的柏克,而是现代的罗素。 丁文江估计罗素来华的影响,是夸大了些。当时情况下,罗素不可能在逼窄如中国的思想小峡谷中赢得多少真实的掌声。尽管如此,倘若实在要找出一个较能全面体现罗素精神的人――既不放弃知识关怀,又不因此而放弃社会责任,既履践社会责任,又不因此陷入革命狂热――,可能还真不是那些一线领袖,而是像丁文江这样的二线人物。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历史中,丁文江是个很值得注意但至今还没有引起注意的人物。在学理层面上,他有形而上眼光,能够超越实用主义的狭隘眼界,领会罗素纯哲学价值。这在当时并不多见,甚至超过了胡适。但在实践层面,他又是个最具形而下实干精神的人。五四之后,他提出中国的责任不在武人、政客,就在几个有责任能力却不敢承担实践责任的知识界领袖,“天下事全看我们‘少数人’的志气”。能够这样看天下者,就不仅需要知识,还需要一点胆识。而知识与胆识的关系,大概是十桶知识也未必换来一滴。他发表“少数人的责任”一文,以及后来的“好人政府”主张,明显有罗素“一打好人”思想的痕迹。他提倡知识精英走出象牙塔,面向大众,承当改良社会的实践责任,点着胡适的名,告诫青年“不要上胡适之的当,说改良政治要从思想文艺下手”。经如此棒喝,胡适之从善如流,方承认丁文江坚持的认识――社会改革只有在一种政治进步的环境中才能成功――有几分道理,于是南下上海,协助丁文江创办以社会评论为主的《努力周刊》。《努力周刊》每期一篇社论,点评一周大事,文风朴实明快,几与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口语相通,其栏目名称就叫“这一周”。如此朴素而又醒目的栏目,现在岂能多见?这样优秀的地质学家,才是真正贴着地面运行的人。后来,即以《努力周刊》为阵地,丁文江、蔡元培、胡适、梁漱溟、李大钊、王宠惠、罗文干、陶行之等十六位中国知识界著名人士一九二二年五月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酿成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稍为有点模样的自由知识分子运动。此时距罗素离华,已经将近一年。之后,再出现梁漱溟的乡村建设,陶行知的平民教育,以及胡适之在《努力周刊》以后的《独立评论》等等,都可以看作丁文江所呼吁的“少数人”起来承担“责任”,或者说是罗素所希望的“一打好人”的实践运动。像丁文江这样的“一打好人”,在今天的聪明人看来,几乎是一打幼稚的童话,至少是不识时务,说不定还有法兰西嫌疑――“不守学术本份”。然而,他们所具备的形而上学理背景一点不比今人薄弱,当年却能扑下身在形而下层面实事实干,这才是罗素精神的真正传人,亦是中国知识界最难产生而又最需要产生的人。 可惜,正如常识所知道的那样,他们都已经死了。
Chen致赵元任,一九二○年十二月十日,原件存罗素档案馆) 感觉苦恼的不仅是中国学界。献花、掌声过后不久,罗素自己的感觉也逐渐败坏。从来华第三个月、赴京第二个月起,罗素即开始有怨声:“当一切都变成了例行公事,中国的欢乐便消失了。”(一九二一年一月三十一日,罗素致柯莉)他感到,与北京的学生们在一起,对他本人的哲学进展毫无帮助,因为中国学生的基础知识太差,真正能领会罗素纯哲学的中国人其实很少,与他们讨论高深的哲学实际上是徒劳无功。罗素原是应邀到中国来讲述哲学课程的,但他刚来中国就发现中国的主顾们兴趣不在这里,“他们不要技术哲学,他们要的是关于社会改造的实际建议。”(罗素致柯莉,一九二○年十月十八日,原件存罗素档案馆)罗素断言,“中国非常压抑,它正在朽败腐烂,就像晚期的罗马帝国一样。”(同上,一九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对于那个名盛一时的“罗素哲学研究会”,罗素后来也不无揶榆,说他们“除一位逊位皇帝的侄子外,全都是布尔什维克分子”。他个人对布尔什维克分子抱有西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特有的同情,当时还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帮助过中国学生进入苏俄。(Chen
Ting-Fan致罗素,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此信对罗素的帮助表示感谢,原件藏罗素档案馆)从他的小册子《共产主义理想》曾被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人当做传单印发,甚至可以推测他已知悉中国共产党当时在上海的创建活动(见《先锋日报》(Dairy
Herald)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九日)。但罗素的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信念使得他最多同情这些新的政治势力,不可能直接主张中国人组成像苏俄那种党纪严厉的政党并诉诸武力。至于北京学者群中的社会主义,罗素观感更为不佳。一九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致柯莉信中,罗素写道,中国的社会主义者“两手抱胸,高谈阔论社会主义,而日本人、俄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则都忙于掠夺中国的富源”。 使人气馁的是,罗素甚至还透露出当时在华的杜威表面上不说,骨子里也有同样的失望:“中国人没有心肠、懒惰、不诚实。他们将赈灾事务全部推给欧洲人,而且他们的政府极端腐败。绝大多数学生愚蠢而又胆小。我并不真地认为我在此间所做的一切有什么价值。杜威夫妇在此呆了一年,他们已完全失望。”(罗素致柯莉,一九二○年十二月三日,原件存罗素档案馆) 这场“西方思想在中国的经历”,实际上是在还没有结束时就已经结束了。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可能得从罗素在华讲演的总体内容去寻找。罗素在华发表的哲学主张以五大讲演著称:《哲学问题》、《心之分析》、《物的分析》、《数学逻辑》和《社会结构学》。此外,为满足中国人当时对社会政治思想的渴望,他有过两场关于布尔什维主义的讲演:《布尔塞维克与世界政治》、《布尔塞维克底思想》。告别中国时,发表具有临别演说性质的《中国到自由之路》。综合这些言论,他的总体特点是: 第一,在哲学方面,神秘臆想被拒之门外,只有具备较高的自然科学素养才能登堂入室。罗素是由数学入哲学,而不是由文学入哲学,他所认可的哲学是建立在自然科学最新经验的基础上,与玄思冥想无缘。他拒绝黑格尔式的欧陆哲学,开辟了数理逻辑实证主义。对于听众而言,连杜威也承认:“有人说,世界上真能够懂得数学的哲学的人,至多不超过二十人,我既不是二十人之一,我也不能懂得。”(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第二,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既同情苏俄革命者的社会主义理想,亦批评苏维埃政治体制的压迫性弊端。罗素来华前曾经专程访问苏俄,对苏俄模式有褒有贬。让中国听众困惑的是,他不认为苏俄的弊端是出于对西方主流文化的反叛,相反,他认为苏俄的弊端――政治权力的高度垄断――是西方财产寡头体制的翻版。他是最早向中国建议采纳俄国人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人,然而,也是最早提醒中国防止俄国政治弊端的人。这样的观点反映了一次大战后西方优秀思想家对社会主义理想的普遍向往,同时亦保留了英美自由主义传统的可贵底色。这与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大幅摇摆,要么是西化,要么是拒斥西化的俄化,有一段很大距离。 第三,他强调知识分子的实践精神,厌恶中国人的坐而论道。他在梁启超、丁文江给他举行的饯行宴席上说,中国要有“一打好人”(GOOD
MEN),敢于承担责任,敢于将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临别演说《中国到自由之路》对中国人提出十几条建议,最后一条是把那“一打好人”扩大为“一万名果敢坚毅之士(RESOLUTE
MEM)”。然而,这样的“一打好人”、“一万名果敢坚毅之士”,肯定不是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家,而是像罗素在英国参加的费边社式那样的知识分子,有自由主义理念,又能脚踏实地,坚韧渐进。 不难想象,中国听众面对这样的讲演,会出现什么样的面部表情。尽管听讲人数不会太少,但是内心的疑惑与误解则难以掩饰。中国的知识传统以文学性文人型著称,而不是以科学性学者型见长。它能哺育出大批文人,乃至过剩,却难培养出在质量与数量上合格够用的学者。由此养成的中国知识传统,实际上只成就了一个文人传统,而不是学者传统,至少前者要比后者强大。每当思想激荡的年代,涌进哲学大门的多是文学青年,至今还是如此。要无数文学青年像罗素那样以冰冷的数理逻辑来思考纯粹哲学,建立纯粹的知识关怀,而且还要拒绝与文学化思维特征天然接壤的欧陆思辨哲学,就“事”论“事”,不能玄思冥想,真比杀了他们还要难受。即使在今天,大陆知识界也还是如此,未必能达到罗素的要求。此其一; 其二,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他固守英国哲学传统中源远流长的怀疑精神,同时亦不缺乏法国人文传统中的热血担当。他号召中国人迅速发展工业大生产,同时又劝中国人警惕社会有机化对个人自由的侵害;他建议中国人效法苏俄走“国家社会主义”的捷径,同时又指出“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并不美妙而且病弊丛生;他鼓动中国人迅速培养起爱国热情,同时又要求中国人必须将爱国热情严格控制在适足以救国的高度;他赞成中国人从事社会政治运动,但又要求中国人保持平和沉静的心态;他希望“少年中国”中间产生成千上万“果敢坚毅之士”,但又避而不谈他们是否应该组成纪律严明的政党。 这样一种社会政治思想,如果一定要放在英美模式与欧陆模式的对立背景中考察,可以说它既非英国的保守主义,又非法国的激进主义,实际上剔除其各自负面因素,综合了两种知识传统的正面因素。对于当时习惯于非此即彼的中国人来说,这样综合性的思想主张,实在是难以把握。 其三,论实践履行,罗素与中国人面对黑暗专制的传统态度也有距离。中国人的习惯:不是去造反,就是受招安,要么揭杆而起,要么缩头作犬儒,独缺当中那种既不制造革命又不接受招安,耐心对峙,长期渐进的坚韧精神。作为费边社成员,罗素赞成的实践方式是:每天前进一寸,不躁不馁,既不狂冒进,亦不受招安;面对不良政治,纵使十年不“将”军,却无一日不拱“卒”。要中国人接受这种费边式的耐心、沉着、坚韧,非几代人的磨砺,难以实现。 罗素可能不知道,这些一时无实用价值的思想,对中国人早说了八十年。就中国人的思想长程需要而言,罗素这些西方思想,倒像中国人所说的“中药”,治本不治标,就中国人当时的短程需要而言,反而是一副陌生而又遥远的“西药”,远水解不了近渴。一直到现在,大陆知识界也未必具备这样的平衡能力,在知识关怀与社会关怀两个方面,能够兼行并举,于此同时,在道义承担与渐进实践之间,又能保持必要的张力。相反的情况倒时常看见:社会情绪高涨时,纷纷放弃知识关怀与渐进实践――见好就上;社会情绪一旦低落,或者仅仅是暂时转移,则纷纷躲避甚至责难社会关怀与道义承担――见坏就收。能够克服这种陋习,在上述两个层面上始终保持平衡,培养一种真正英格兰作风――见好就收,见坏就上,而不是相反,当然殊非所易。然而,这又是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衡量知识界是否成熟的标志之一。 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罗素给英国情人的信中说:“患病之前我就已讨厌中国的北方了,这里很干燥,而且人也冷酷无情。我深感疲惫,归心似箭。”(罗素致奥托林)不难想象,罗素在华十月,表面虽然热闹,内里知音难遇,甚至连象样的对手亦难寻觅。其实他是半年不到,即萌去意,后来因病拖延五月,亦如置身沙漠,只盼早归。拖到七月,能够策杖而行,终于告别中国学界,与杜威同日离京。 罗素怏怏而归,心情不会愉快。离开之后,中国知识界亦觉尴尬,对他的影响力大小发生过一些争论。由梁秋水当社长而雇佣外国人JOSEFW.HALL当主编的英文报纸《北京导报》,于一九二一年八月四日发表了一篇社论,说罗素的思想并未为中国的青年所欢迎,罗素对中国并未产生深远的影响。丁文江在该文发表的第二天即致信《北京导报》编辑部,要求他们撤回这篇评论。丁文江指出,罗素在哲学和社会思想方面必将在中国造成既深且远的影响,正是罗素使中国人第一次认识到哲学应该是对所有科学进行综合的结果,社会改造必须以丰富的知识和深思熟虑为前提。“罗素学说研究会”的成立、罗素演讲录的广泛刊载和流传、罗素患病所引起的普遍忧虑、罗素发表告别演说时听众的拥挤程度,都表明罗素深深地打动了中国人的心灵。(丁文江致《北京导报》编辑部,一九二一年八月五日,原件存罗素档案馆) 平心而论,丁文江过高估计了罗素在华影响。这位在英国受过良好训练的科学家可能是按着他自己对罗素的深入理解,来理解中国听众的理解能力了。 不妨承认,罗素的中国之行是以两方面的失望结束,而中国人的失望甚于罗素,是一种双重失望。 七十年前的中国人感到失望,是因为罗素没有提供一个一面倒的意识形态,不解渴;七十年后的中国人忙于以激进与保守的二分模式切割五四思潮,同样会感到失望。因为无法把他捺入一个要么激进要么保守的简单模子里,甚至会感到恼火。怎么会有这么一个思想家呢?既激进,又保守,或者说既非激进,亦非保守,说他是个激进的保守主义者好,还是个保守的激进主义者好?既有英国人的冷静,又有法国人的热血,或者说是既非英国,又非法国,他是个英国式的法国人呢,还是个法国式的英国人?既然有激进色彩,为何受中国的激进主义者冷遇?既然有保守主义倾向,为何又得不到中国保守主义者欢迎?太让人别扭了。总之,四不像,无论用什么模式都套不进去,让你左右为难,过去为难,现在继续为难,让一切简化模式为难,这才是罗素,这才是真正思想家、真正思想史事件的应有内含。可以说,一部思想史,就是由一系列为难人物、为难事件组成的。罗素中国之行,也许并不成功,但是这场不成功的思想旅行及其主客两方的错综反映,却对那种有关英法知识分子传统、有关五四时期中西思潮交汇的简单化模式,构成了一个有趣的挑战。它促使人们重回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贴着地面运行,怀疑那种非此即彼的二分法;问题一旦想得复杂,那种不是激进就是保守的僵硬模式就会松动;某些似是而非的虚假学理――比如说以批评五四激进主义为名,张冠李戴,暗行绥靖思潮的时髦观点,也就多少露出一点破绽了。有这样一条积极意义,罗素一九二○年的中国之行,不也留下了一些可取之处吗? 是不是罗素太特殊,不能代表英国思想家保守主义的集体性格呢?也未必。英国哲学家柏克的名字现在是京沪知识界较多引用的一个热点。就我所知的有关柏克那一点史料,我觉得大陆知识界对柏克的热衷,似乎也不全面。人们感兴趣的是柏克抨击法国大革命的那篇在英国议会上的讲演,但是忽视了柏克曾经热情支持过美国革命反叛英格兰本邦,而且与十八世纪最激进的流浪革命家潘恩一度是莫逆之交,当国人皆曰可杀时,柏克就为潘恩提供过自己的庄园,衣食住行,好生款待。英国知识分子未必都像中国知识界在今天所想象的那样冷血,连柏克都有另外一面。保守主义者多半出身贵族,在政治风浪中,且不论政见离合,对待落难对手,起码具备骑士侠义的一面。离开这一点而奢谈保守主义,只会让这些昔日贵族讥笑为小郡市民的假冒伪劣。当然,真正能够避免法国知识分子的革命狂热,同时又能凸现知识分子社会良知的典型,确实不是古典的柏克,而是现代的罗素。 丁文江估计罗素来华的影响,是夸大了些。当时情况下,罗素不可能在逼窄如中国的思想小峡谷中赢得多少真实的掌声。尽管如此,倘若实在要找出一个较能全面体现罗素精神的人――既不放弃知识关怀,又不因此而放弃社会责任,既履践社会责任,又不因此陷入革命狂热――,可能还真不是那些一线领袖,而是像丁文江这样的二线人物。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历史中,丁文江是个很值得注意但至今还没有引起注意的人物。在学理层面上,他有形而上眼光,能够超越实用主义的狭隘眼界,领会罗素纯哲学价值。这在当时并不多见,甚至超过了胡适。但在实践层面,他又是个最具形而下实干精神的人。五四之后,他提出中国的责任不在武人、政客,就在几个有责任能力却不敢承担实践责任的知识界领袖,“天下事全看我们‘少数人’的志气”。能够这样看天下者,就不仅需要知识,还需要一点胆识。而知识与胆识的关系,大概是十桶知识也未必换来一滴。他发表“少数人的责任”一文,以及后来的“好人政府”主张,明显有罗素“一打好人”思想的痕迹。他提倡知识精英走出象牙塔,面向大众,承当改良社会的实践责任,点着胡适的名,告诫青年“不要上胡适之的当,说改良政治要从思想文艺下手”。经如此棒喝,胡适之从善如流,方承认丁文江坚持的认识――社会改革只有在一种政治进步的环境中才能成功――有几分道理,于是南下上海,协助丁文江创办以社会评论为主的《努力周刊》。《努力周刊》每期一篇社论,点评一周大事,文风朴实明快,几与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口语相通,其栏目名称就叫“这一周”。如此朴素而又醒目的栏目,现在岂能多见?这样优秀的地质学家,才是真正贴着地面运行的人。后来,即以《努力周刊》为阵地,丁文江、蔡元培、胡适、梁漱溟、李大钊、王宠惠、罗文干、陶行之等十六位中国知识界著名人士一九二二年五月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酿成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稍为有点模样的自由知识分子运动。此时距罗素离华,已经将近一年。之后,再出现梁漱溟的乡村建设,陶行知的平民教育,以及胡适之在《努力周刊》以后的《独立评论》等等,都可以看作丁文江所呼吁的“少数人”起来承担“责任”,或者说是罗素所希望的“一打好人”的实践运动。像丁文江这样的“一打好人”,在今天的聪明人看来,几乎是一打幼稚的童话,至少是不识时务,说不定还有法兰西嫌疑――“不守学术本份”。然而,他们所具备的形而上学理背景一点不比今人薄弱,当年却能扑下身在形而下层面实事实干,这才是罗素精神的真正传人,亦是中国知识界最难产生而又最需要产生的人。 可惜,正如常识所知道的那样,他们都已经死了。
声明:在澳纽网频道上发表的内容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的目的,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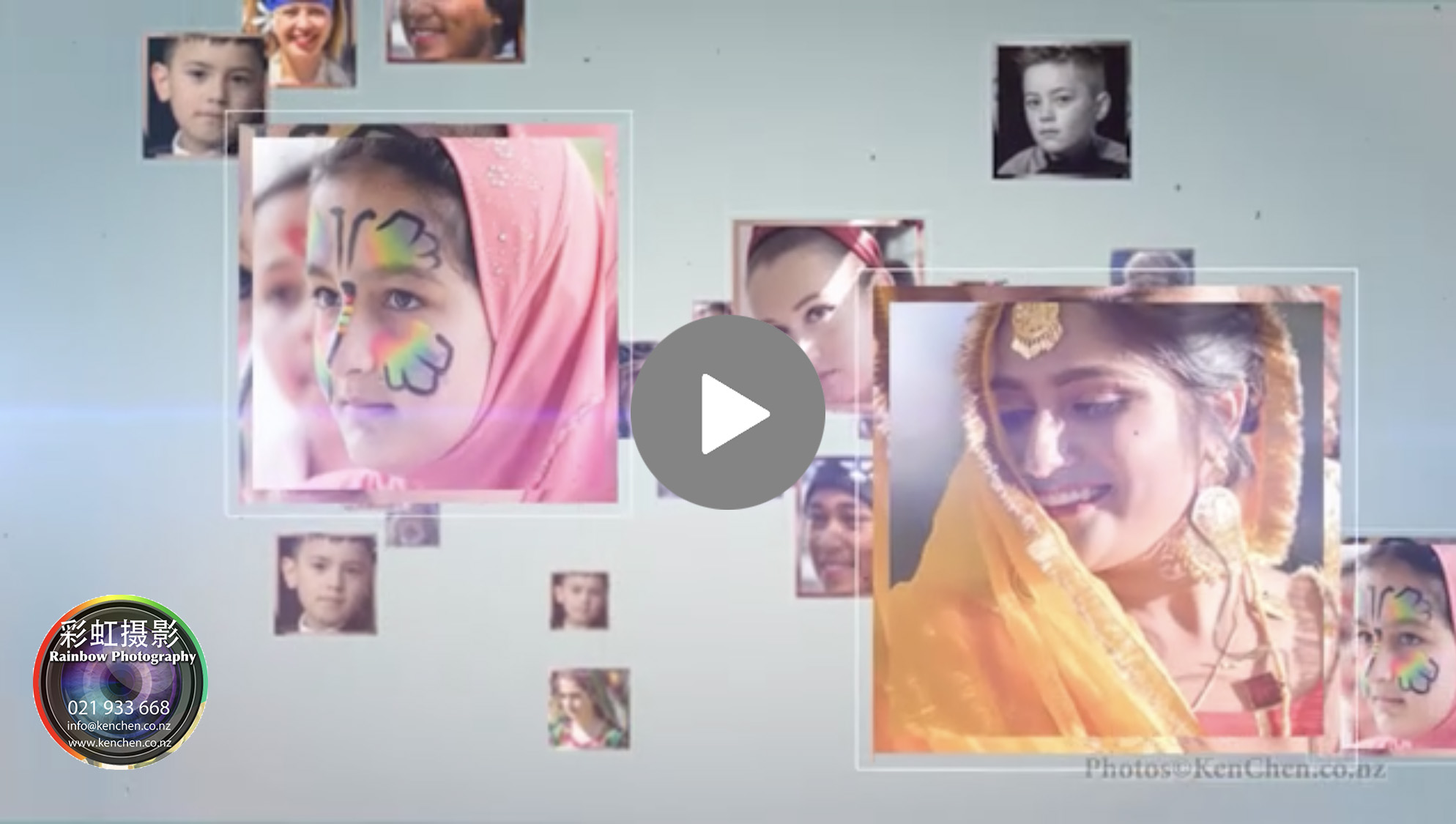


感谢您对澳纽网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