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新西兰旅游 > 畅游群岛湾
作者: 李耆 人气: 2556 日期: 2013/9/9
下午一点半,游船便缓缓地离开了奥普瓦(Opua),行驶在群岛湾(Bay of Islands)的海面上。透过窗玻璃,我尽情地观赏了南太平洋的海上风光。对照一位船员向我们提供的地图,我知道船只离开奥普瓦之后,向东北驶去。游船缓缓地穿过了派希亚(Paihia)和拉塞尔(Russell)之间海湾,抵达塔皮卡角(Tapeka Point) 的近海之后,便转向东方行驶。游船 穿过莫图瓦罗赫瓦岛(Moturohia Island)与奥罗卡瓦湾(Orokawa Bay)之间的水道后,又越过莫图罗阿岛(MoturuaIsland)和暗杀岩洞(Assasination cave)之间的航道。游船直到抵达贴近乌路普卡普卡岛(Urupukapuka Island)的奥特赫依湾(Otehei bay)的海面上,才停下来。这一段航程有多少海里,我不知道。只晓得,大船在海面上航行了约一个半小时。
开始,我坐在床上,倚着窗台,透过右舷窗,看到窗外的大海和岛屿,景色美不胜收。游船浮动在群岛之间,宛如进入了人间仙境。我住在游船的底层,海平面离我的身子不过一、二米。我想,窗户如果可以打开的话,伸腿便可洗脚,伸手也可舀上一瓢海水。如今,隔着密封的舷窗,透过洁净的玻璃,我静静地俯视着海水沿着船舷往后飞奔。我知道,它将 消失在螺旋桨卷起的怒涛之中,完成它的历史使命。隔着玻璃窗,抬头往海面望去,海水的色泽由淡而深,由浅蓝而深蓝,一直从近处伸展到远方的小岛脚下,变成了深不可测的迷蒙一片。往日在海边常见的那种流光铄金的景象,今天已不知去向。因为天上正在下着雨。雨势还不小,密密麻麻的雨点,像神仙从天空向大洋撒放着大把珍珠,在海平面上溅起无数个水花。水花,水花,让人遐想无穷。我坐在床尾,下巴倚在窗棂上,双眼沿着船舷往下望。我估摸了一下,眼睛离洋面不过三、二米。洋面上的一切,我都看得清清楚楚。宽阔的洋面上,布满了白头浪。看来,两三天前在斐济等岛屿上肆虐的台风,现在吹到了群岛湾。我们的运气真不“错”,正好遇到了它。也好,接受挑战吧!
现在的洋面上,不仅雨骤,而且风狂。从东北方向刮来的大风,猛烈地吹拂着海面。狂野的大风,对海面过分热情地亲吻着。大风对海水一阵又一阵地吮吸着,海水随之被吸向空中,卷起了一波又一波巨浪。每一波巨浪,贴近海面的基底,宽广厚重,风将海水往上拉升时,出现了流线型,到了顶端,便相当薄了。我从船窗往外望,看到的正好是浪头的侧面。我发现,每一个浪头,竟然很像一把刃口指向上天的板斧。在浩渺的洋面上,布满了这样的“大板斧”。板斧的刃口,都涌满了白色的浪头。一霎时,一波接一波的白头浪,布满了宽阔的群岛湾的洋面,场面极为壮观。它带给人们精神上的振奋,绝不低于微风吹起涟漪的洋面给予人们的恬静感受。游轮经过的航道,两边都有海岸或岛屿,我住的卧室,在游轮的右边,所以在游轮从奥普亚到奥特赫依湾的这次航行中,我看得到的只有拉塞尔。我原以为拉塞尔是一个岛,其实它只是一个半岛。在历史上,拉塞尔很有名气。 拉塞尔,毛利人原来叫它为克罗拉瑞卡(Kororareka),意思是“美味的企鹅”。1840年,怀当义(Waitangi)条约签订后,这里曾被定为新西兰的首都,并被命名为拉塞尔。不过,仅仅过了一年,首都就被迁到奥克兰去了。首都一去不复返,此地空余新地名和显赫一时的历史。
拉塞尔半岛上,树木茂密,郁郁葱葱,极目望去,尽是翠绿。绿的山峰,绿的缓坡,绿的森林,绿的草地,好似一块硕大无朋的绿油油的毛毯,铺在半岛之上。连山上的房子,也有用绿色屋顶绿色墙壁的。只有在绿色毛毯的边缘,镶嵌着一条狭长的飘带。飘带的颜色,淡淡的,黄黄的,我知道,那就是沙滩了。沙滩之外,便是正在承受着暴风雨吹打的海面。在晴日,这儿的海面,也许是一片蔚蓝。但现在,却显得云遮雾障,迷迷蒙蒙。
半岛上,沙滩不多,镶在绿色大地毯边缘的飘带很短。一眼望去,这儿的海岸线上,有突兀独立的悬崖,有伸入海洋的缓坡,有离岸矗立的巨石,有突入水中的尖岬。真可谓犬牙交错!
极不规则的海岸线,激起了人们更多的遐想和好奇。
可惜今天,天不助我,风雨太狂,无从深究。我想,暂时留下这个遗憾,另选一个丽日晴空、艳阳高照的日子,重游群岛湾。
声明:在澳纽网频道上发表的内容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的目的,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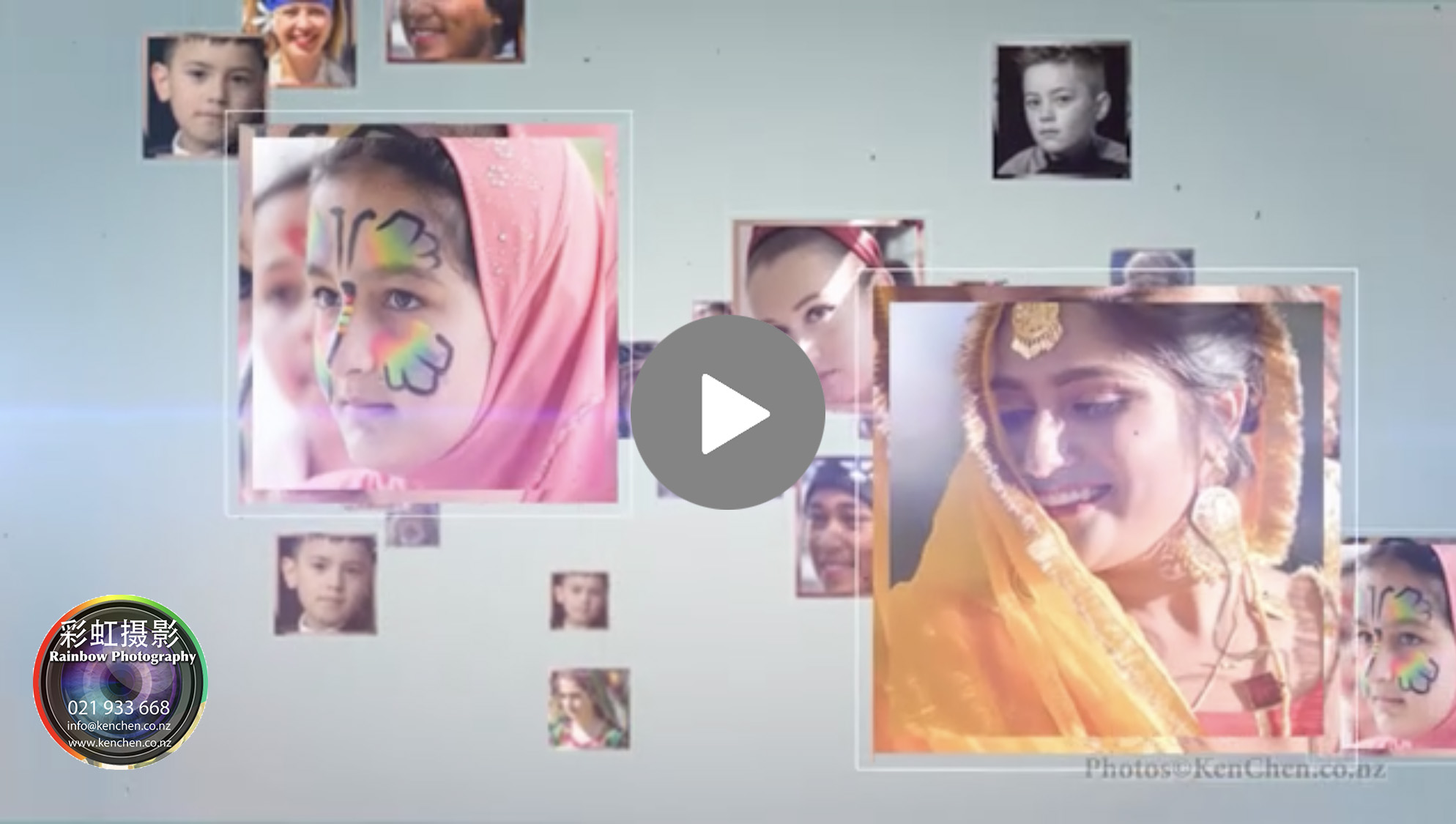


感谢您对澳纽网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