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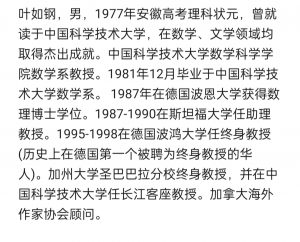
叶如钢自选诗|美国
麝香—从彼岸移植过来的唯一花朵
一个灵魂终于抵达彼岸
就有一朵彼岸花在此岸开放
它的颜色是灵魂颜色。或者无色
除了在静夜,犹如脱去衣饰的洁白
当一个灵魂抵达彼岸,有灵魂的香归返
彼岸花的高贵不能成就为香料
它唯一的失败方式是拒绝香
它也以失败的典雅抗击现实的残酷
灵魂的归香,必然是一种极致的抽象
也在风中的具体细草、心灵香孕的枯萎
把一切生命征象析出,最后的存在
若你的夜晚里,彼岸花开
而没有任何噩耗、也没有香袭
若彼岸花遥远,但它摇曳、不可抗拒地进入思维
它并不是属于你的象征
仅仅需要把你的手指浸入水,更深地
更白色。更轻地让我握住
你沐浴纯粹的光辉
在森林的蓬勃和宁静孕育
你在午后的睡眠之雪
死亡和其他象征都断成松花、细的松针
你作为细致的生命象征并且快乐地奔跳
你并且是世界无法抗拒的香的孕育
然后你的香一瞬间穿透每一古典和每一现代
你并且是我认识的最后的美
(原载百科诗派“香料史“【总第27期】)
我听见
这暗色的夜里深藏明亮,因为听见你的美丽
雪落之后没有声音,因为落雪是最后的声音
但是我听见你的美丽
貂鼠从青檀木跳跃,或者说飞,落到更高的杉树
我听见你的玻璃器皿
我听见南方,一连串南方刨木花四下里飞溅
我不敢用宗教青铜敲击它们
虽然你会在内心里命令我敲击
花豹和刚毅的信使拥抱后在南方山坡上袭击野羊
我听见你的复兴印象从岩石上一片片落下去
我听见北方,被大水洗白的北方
在白色的地方总是能听见你的白色
睡莲
倘若是水,我可以承载我的女人,不计较她暴食后的体重
我的女人便是开蓝色花的睡莲
她若宁愿是水,作为水超过她的所有可能
我则命定不可能成为她的睡莲, 不管选择的什么颜色
我的睡眠,被她作为水卷入她双目之间,作为睡莲轻抚于她双乳之间
或者她作为水的表面把我密切地全部包裹
她轻唤我的小名
作为水她更赋予蓝色睡莲的死亡
她遵循自然法则爱我、对我严厉
她严重地违反自然法则
没有做我的女人之前已经成为睡莲
作为我的睡莲,她最热衷的游戏是夜晚分成很多株
作为水,她也是我的莎草纸
忘记我时, 她是画里的静物
钉子辞
把钢轨钉住的铁铆钉。由此进入
无国藉月光与夏季末零点列车的定性
拆开木建筑,撒在地上的木楔钉
身体里固定骨板楔入的钢钉
由此参与了身体和精神所有的柔软契约,牵制阴谋,涌荡
密密麻麻而间隔的钉子排列广大平面
钉子断崖般失去钉头
钉子的白壁、夜幕,和萌芽地理,不能不作为喻写图卷曲
固定神手掌、人心脏和兽角的钉子
悬挂现在进行时礼服和将来时态马匹的钉子
沉默时刻
过度理解沉默的意义,以至于已将其从清华简里取出解构
在较少挑剔、较少繁琐的场合,沉默的华丽时刻是一枚鲁伯特之泪
貌似融化后忽然凝固的脆弱玻璃,却绝对地坚不可摧
这正如众鸣蝉集体在大水里取出幸存的新壳
但在生命最光辉的时刻击碎神秘之尾,忽然崩溃成一地不朽的细雪
这徒然增加了很多未清理的碎片
也提前看见豹子的额头纹和鹰的眼珠
宏大的生命和细小生命一样从来只有蛋白质的沉默组合图像
花都从春季进化到夏季获得了颜色的新型悲喜剧意义
犹如中古征服者舰队的某一时刻,碧蓝色山壁向下流动的水是不动和沉默的
从远处看细节都隐藏起来,让宏观结构显现
进入每一个细节,或者狂喜,或者是煎熬的炼狱
列车
在宏大生存空间的坚硬表面做集体快速冒进
这本来是穿过地理和宗教的山岳、凌驾于地质和哲学的大河
更可以把全部旧式抽象装进去而向新空间突袭:
生锈时钟里收集的时间纽结和鸟类时间片
不断融化的意外矿物,冰川上开放的冰藻丽色
最初非常细碎,然后独自无止境蔓延
最初没有明确色彩与格式
然后不断重叠东方女人夏季裙,放弃任一种掩饰
或然这是一列奔腾的妩媚母豹,把人类作为子女抱进来
宁静的母性和暴烈的兽性可以交叉
皮草和植物性的自由元素可以一起重新装置艺术
经过一番载物、载思和撕咬,以废弃精华的形式完整吐出
就像现代高层建筑、六朝壁画和弯折街巷的文化因子与百部格式被装进来
并且卷曲的水面被当作异域古代地毯在列车里卷开
车窗被新鲜的风打开,包藏的枝节伸展出来绽放
母性猛兽之后是翻过山的野驴和羚羊
列车之后是无情钢轨、枕木和从世间到世外的剩余镜像
鹤与爵, 因为易客
白鹤翅膀底的黑色作为顽强提示
当闪电击中不存在的雕像,鹤从一层暗树飞到下一层明亮的树
我不经意地路过, 看到黑暗里的欣欣向荣
某些语言,集体和我的口舌第一次相对
当我从薄纸里提取最后水分,你会意一笑
好像某世纪的贵族骑士
旷地有你企图种植的植物穿过我冷塑的玻璃手掌
我们把一切有意义的东西用水面包裹
把一切无处托付的东西用新刀分割
你有一头愤怒的豹,我有一头妩媚的豹
你的命运猛于虎, 我的北方虎张开全部虎骨
我将导引狮子。失明后让狮子导引
我将陪伴鹤在西伯利亚飞行
以爵燃烧干冰
无底的思想将在墓地生长为宁静的百合
稻谷赋之词汇赋
稻谷词汇,和脱壳之后的米粒词汇
可以喂饱世界各族各部落语言的全部词语
黄色人种的语言是黄色的,土黄色和金黄色, 所以直接以稻谷词汇喂养
粗犷的亚洲部落人语言, 以更深色的野稻词, 那种雄性不育的稻种
并且可以和非洲语言、西方语言杂交
即使你不乐意待见, 语词的原始生命比野草、比发情的野兽更强劲
不错,黑非洲语言需要黑米词汇,比众乌鸦更不可一世的黑色词语
在黑米堆面前, 黑色的死神也是一只最小的乌鸦
而西方的白色语言, 非常白的语言, 即使掺杂了现代、后现代的变种仍然那么白和惨白的语言
不妨继续以脱壳的白米粒词汇喂养
简单地喂养即可, 不必考虑稻谷的杂交, 比如莎士比亚的语言、巴尔扎克的语言、恶之花语言、百年孤独的语言、策兰的语言、布罗茨基的语言
与真实的稻谷相比, 概念都是平行的, 比如刚刚阐明黑米对应乌鸦, 白米对应西语之花, 以及各类惨白的鸟、白色布匹、各族类的洁白女人
与真实稻谷的非凡人物让众人敬畏、顶礼膜拜相比,稻谷词汇由每一个青蛙重新创造,虽然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语汇继续灌浆
稻谷词汇丰盛收获,或者遭遇极度干旱、无法抵挡的洪水,而让诗者全部哑口无言、无字可写, 这只能暗示一下
白草赋
1)
白草。若想象倾伏于沙质地的一种干燥信仰
若想象在大风里展开身披白袍
就手握一把白草的白穗,一把紊乱、茁壮的白草
也可以用现代理智把它们梳理
若贫穷或被困、处于饥渴绝境,渴望抚摸白金
若至暗,祈求死亡月光的具象复活暗示
若孤独、凄楚,渴望亲近女人的洁白丝衣
或手抚一丛白草的白穗,把灵魂底色变白
把精神的钢刃拉伸为一根根白草刃
“白草城中春不入”
“边马仰天嘶白草”
2)
黑沙蒿的群落、白沙蒿的湿沙固定堆积
在西域,在鄂尔多斯高原
前方是蒙古高原,后方是黄土高原
前面是深一层的青草,后面是深一层的水域
青草、白草、白草,在广大地面
在无以复加的天空俯瞰之下
若想象自己的兽性,或可温驯,以白草喂食
若想象自己的内火不可抑止,有白草为药
这是白色的精神斜坡
这是虚无、实在的交错生长和消没,仅仅涂了白色
“千山万碛皆白草”
“白草连天射雁归”
3)
没有白梨花的时候,有白草
没有白荷、白玉兰的时候,有白草的白花穗
没有经卷让风卷时,风卷白草
没有中亚狼群时,白草像狼尾巴依偎
白骨被时间吞噬完后,有召唤的白草
白银长尺,沿着白草的长叶茎测量
白草的白穗积聚起来,让月光照射
没有女人的洁白面容时,有白草的白花穗
没有白鹤飞舞时,有白草飘摇
没有安静的白虎时,有白草高原
这是灵魂的水银,在未来的背面
“鸢觑败兵眠白草”
“白草山头日初没”
(原载百科诗派“草木也古典”【总第33期】)
植物志之榕树
写在白纸上的字词犹如榕树种籽写于土地
字词可在纸面之外萌芽犹如榕树种籽可在土壤之外萌芽
倘若乌鸦或秃鹫叼去字词,也就像叼走榕树种籽
榕树从它的枝干生出气根长须,只有惊奇的形象,不具备被形容的可能
这意味着它的飘逸、自由、随性
意味着它的野蛮、无视一切。或者说无敌
植根于此的语词与逻辑只能在内部寻找更高的形式
犹如它会给人类喂食夏季结束的雨水、冬季任何时刻的雪
榕树的须而又须具体和抽象目的皆在垂直的下方
榕须,纤细手指,青春和枯萎同时的手指,即将接触、抚摸土地
接触、抚摸后就抓紧
那种颤栗抚摸、倾心依贴与暗自惊心动魄的汇合在人类的体验之外
人类的无穷幻想体验和倾诉正是不可替代的自我救赎
任何这样一种神性接触
任何在一个局部安静、兀自注目的倾覆之力
榕须长成笔直的臂。笔直、俏丽的腿
长成挺拔的身。美的身姿。众多的身姿
以亲切、淡定神态邀人类纯粹、灵性地接近
它创造的陌生清廓空间充满距离和非距离
它美好的皮层里有丰满白色乳汁
从一棵榕树涌现为构成一片大境界的榕树林
也独自粗壮、宏伟地向上,向四方蓬勃伸展枝干
巨大的绿色伞状皇冠。宁静的皇苑驯养一群自由自在高马
它有时也被驯服为独自向隅而思的矮型植物
把所有的可能缩小为一个拥抱自己的姿态
一束束阳光把榕树细叶渐次,或逆序敲响
鸟雀飞向它,被它关怀和超度
众花朵展开色彩和繁复形象
榕树花在五月开放,榕果在六月成对腋生
缩小之后的榕树没有花朵和种籽
没缩小的继续宏大、上升,众种籽任性、野蛮地播撒、蔓延
榕树仍然经过向下再向上生长成众多的俏丽
它凸起的众板根仍然盘根错节布满大片地面
它仍然面向种种生存可能做最可靠的选择,和意外的新选择
新西兰 澳纽网出品
编辑:小图
1,249 view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