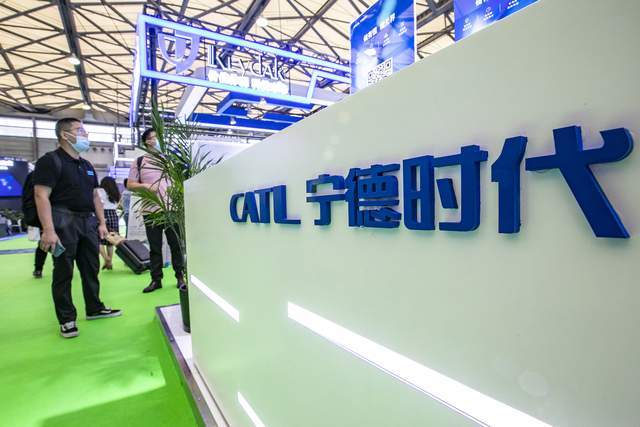第75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的颁奖典礼上,陈剑莹是第一个走上奖台的获奖者,她的作品《海边升起一座悬崖》摘得最佳短片金棕榈大奖。颁奖前一个小时,她接受了我们的专访。
陈剑莹回忆自己对电影的热爱,大概最早来自环境的潜移默化,因为家里开店卖DVD,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艺术背景。她有着高效的执行力,95后导演,却已经拍过多部短片并在各大电影节上获奖。她说拍片从没有找家人要过钱,15岁就一个人跑到北京拍片,自己找来团队,又将拍摄的短片做成DVD,包装好,拿去推销,挣来的钱还给父母。大学三年级开始,她已经在外面接拍MV的私活,每年挣的钱足够维持自己的日常生活开支,从此不再需要父母支付。陈剑莹还是一个忠诚的合作伙伴,这一次获奖短片的制片,正是十多年前她初拍短片时的朋友。
 众多成功人士的复杂和悖论,在95后的年轻导演陈剑陈剑莹身上同样可以看到。瘦小娇弱和出现在社交场所的摩登表象下,隐藏着强大鲜明的个性和做事的极端严谨专业。人如其名,有如利剑般的果决和坚韧,也有如水一般的晶莹和变幻莫测。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缪赛、叶芝或者余秀华的诗……文学是她创作的重要来源,就像古典钢琴音乐会让她在疫情封闭时期,更好地找到自己。温柔的说话、羸弱的外表与内心的不安和躁动互成对应,她不断在矛盾中寻找与自己的和解,也正是这样的碰撞,带给她更多旺盛的创作思考和激情。拍片以来,她也一直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众多成功人士的复杂和悖论,在95后的年轻导演陈剑陈剑莹身上同样可以看到。瘦小娇弱和出现在社交场所的摩登表象下,隐藏着强大鲜明的个性和做事的极端严谨专业。人如其名,有如利剑般的果决和坚韧,也有如水一般的晶莹和变幻莫测。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缪赛、叶芝或者余秀华的诗……文学是她创作的重要来源,就像古典钢琴音乐会让她在疫情封闭时期,更好地找到自己。温柔的说话、羸弱的外表与内心的不安和躁动互成对应,她不断在矛盾中寻找与自己的和解,也正是这样的碰撞,带给她更多旺盛的创作思考和激情。拍片以来,她也一直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不满足停滞的生活,陈剑莹总是在漂泊中,去学习和发现新世界。从18岁选择远渡重洋到纽约大学,19岁独自一人趁假期去伦敦政治学院修学,又到巴黎学习法语,拍摄影片。她在不同的地方不停累积新知识、新体验,2015年还随法国电影发行公司在戛纳电影节实习过。特立独行甚至享受孤独,陈剑莹说自己其实很能吃苦,大一时参加一个拍摄竞赛,就亲力亲为那些琐碎重活。拍片如此,生活中也是,大学四年经常买转机的机票,拖着大行李箱就可以全世界去旅游。投入工作后,她会在疲惫疯狂袭来的时刻,将手机和所有的现代工具关闭,独自躲到无人的大山深处,与世隔绝放空自己。
不满足停滞的生活,陈剑莹总是在漂泊中,去学习和发现新世界。从18岁选择远渡重洋到纽约大学,19岁独自一人趁假期去伦敦政治学院修学,又到巴黎学习法语,拍摄影片。她在不同的地方不停累积新知识、新体验,2015年还随法国电影发行公司在戛纳电影节实习过。特立独行甚至享受孤独,陈剑莹说自己其实很能吃苦,大一时参加一个拍摄竞赛,就亲力亲为那些琐碎重活。拍片如此,生活中也是,大学四年经常买转机的机票,拖着大行李箱就可以全世界去旅游。投入工作后,她会在疲惫疯狂袭来的时刻,将手机和所有的现代工具关闭,独自躲到无人的大山深处,与世隔绝放空自己。
 原本筹拍的长片故事,因为疫情无法进行,对于一个始终在工作的人,她很焦虑,担心自己没有成绩没有进步,尽管这期间,她其实并没有把自己关在家里,一方面参与一些影片拍摄,另一方面自己的剧本创作也从来没有停止。也正是因此,在长片拍摄不能如期进行时,有了这部短片的尝试。《海边升起一座悬崖》讲述了世界末日背景下,陨石撞击地球、江边小镇即将被倒灌淹没之时,姚安娜主演的少女念念,在和家人逃离家园前,去和儿时的伙伴告别,一路上看到不同的人不同的事,过去的美好回忆一点点浮现,激起了她对现在和未来的情绪。
原本筹拍的长片故事,因为疫情无法进行,对于一个始终在工作的人,她很焦虑,担心自己没有成绩没有进步,尽管这期间,她其实并没有把自己关在家里,一方面参与一些影片拍摄,另一方面自己的剧本创作也从来没有停止。也正是因此,在长片拍摄不能如期进行时,有了这部短片的尝试。《海边升起一座悬崖》讲述了世界末日背景下,陨石撞击地球、江边小镇即将被倒灌淹没之时,姚安娜主演的少女念念,在和家人逃离家园前,去和儿时的伙伴告别,一路上看到不同的人不同的事,过去的美好回忆一点点浮现,激起了她对现在和未来的情绪。
 MW:为什么会想到拍摄这部短片?
MW:为什么会想到拍摄这部短片?
陈:因为疫情,好久没有拍片了,就想拍一部。长片太难了,就拍一部短的吧,公司也支持就拍了。最开始想表达悲情时代下的浪漫主义,在这样的状态下还是想抓住一些美好的东西。从这出发我想了一个故事,又对宜宾这座城市很熟悉,因为我的长片准备在这里拍的。那里的气质很合适,我又想把我对中国土地的这种感受表达出来,呈现出诗意的、深情的感觉。这种感受和视觉语言已经在我脑子里面了,故事主线就是一个女孩在城市里游走,一开始写了一个寻找母亲的线,母亲离开这座城市去了外面,后来发现生活的这座城市其实很美好,后来,意象性越来越多,就去掉了写实找妈妈这条线索,而是更多寻找自己,寻找内心的记忆,这个方向定了我们就开始进入编剧了。编剧老师跟我一去看景、去实地采风来充实细节。编剧老师是在我的大纲基础上创作,基本他写几稿,我写几稿。
 MW:我看编剧栏目并没有你的名字?为什么?
MW:我看编剧栏目并没有你的名字?为什么?
陈:因为我觉得从我的大纲到第一版剧本,编剧老师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是他把这个文本丰富起来的,我只是在此基础上再次修改,导演改剧本是很自然的事情,就没有必要去写上自己的名字。这个团队里所有的人都给我很大帮助,没有他们我绝对站不到这里。因为我们要拍胶片,又有上山下海的镜头,所以有一个70多人的大团队,尤其是核心主创团队,大家都给了我很多帮助。
MW:为什么片名叫做《海边升起一座悬崖》,而且它的英文片名“The water murmurs”不一样?
陈:这其实是波德莱尔的一首诗,我喜欢读诗,中外都读,余秀华《摇摇晃晃的人间》、波德莱尔《恶之花》、缪赛、叶芝……我之前在巴黎拍过短片《在亲吻中启程》,也是读缪赛的诗的时候想到的。我读诗的时候就会摘抄下来,像是有个小文库,这是我拍片灵感的一个小集合。后来拍摄这部片子,就想到“海边升起一座悬崖”挺合适的。宜宾是在水边的城市,片名很有画面感,它不是我们通常看到的大浪拍到悬崖上,再升起来,而是海边升起一座悬崖,是倒过来的,有点超现实的感觉。包括悬崖升起来,是很有力量的感觉,就好像内心升腾起一种力量或者说找到自我,它可能可以抵抗很多未来的风雨侵袭,所以觉得跟主题很契合。的确,片子的灵感不是从过去的电影中,而是从文学中获得启发的。
在取英文片名的时候,我不想直接翻译它的中文名字。翻阅了各种诗集都觉得不合适,就想片子里表达的意象有没有什么是我觉得特别重要的,就想到水的元素。我的很多片子里都有水,我对水有种感觉,就是它有穿越时间和空间的能量,翻涌和平静的时候都有各自的力量,是个很神奇的东西。水在这个片中也出现了很多次,就像水在你身边,亲自跟你呢喃很多情绪很多故事,所以片名就叫《水在耳边呢喃》。
 MW:《海边升起一座悬崖》的一开始,姚安娜扮演的念念在海边,我们听到的哼歌是她唱的吗?
MW:《海边升起一座悬崖》的一开始,姚安娜扮演的念念在海边,我们听到的哼歌是她唱的吗?
陈:是我唱的,是我和剪辑师一起写的,我俩一起写的词曲。那天片头拼好后,剪辑师说这里应该放个歌谣,我也觉得应该是这个气氛,两人就开始一起写词,然后觉得应该是哼唱的感觉,那我就哼一个吧。我看着那个画面,现场对着词,就哼下来了。影片中你可以理解成是女主人公在唱,也可以就是这个小镇的一首歌谣。
MW:片子因为陨石坠落地球的设定,本身比较科幻未来,胶片在今天几乎已经是一个历史概念了,和历史年代片联系到一起的更多,你为什么选择用胶片来拍?
陈:因为我一直没有把它定义成科幻,可能有点超现实,而胶片更有那种颗粒质感,更能帮助我营造出这种诗意和超现实的氛围,它会跟人眼看到的世界微微有所区别的,会帮助整体视觉表达,包括所有的颜色,蓝色和绿色,不同的层次感胶片会捕捉得更好,比数码更有味道。
MW:前期筹备会画故事板吗?
陈:会的,我的习惯是在开机前,和摄影师和工作人员对好,把视觉方案做一个非常详细的介绍,它是什么样的质感,有什么样的镜头运动,里面的大多数镜头都是我自己设计的。包括安娜在有鹅的那个蓝玻璃房子里,她这样走过去,然后出画,我们看到鹅,然后再从另外一侧走进来。当然也会和摄影师做其他沟通,但其中有几个从一开始设计分镜头的时候,我就很坚定的镜头,摄影师也非常支持我,按照我设定的来拍摄。安娜第二次去见小少年的时候,镜头从走廊横移过来,看到空的房子,然后有一个敲门声,我们才看到安娜。很多游荡的镜头,包括在绿色房间里,是完全在轨道上进行的。
 MW:是的,我注意到,一般年轻导演拍摄四比三画幅时,最常见的就是固定镜头,而在你的片子中,不光是镜头移动,而且移动得非常频繁……
MW:是的,我注意到,一般年轻导演拍摄四比三画幅时,最常见的就是固定镜头,而在你的片子中,不光是镜头移动,而且移动得非常频繁……
陈:因为我觉得宜宾这个地方会让我有飘浮感,我自己的人生也会稍微有点漂泊感。(这么年轻就有漂泊感?)的确,我的人生一直归属感挺少的,在里面梦境游荡的感觉,这是我的感受,也是我在片子里很想表达的东西。漂泊也好,游荡也好,我希望观众真的能在这一空间里游荡起来,所以最开始想的就是这种飘飘的感觉,镜头缓缓运动。
MW:这一次和姚安娜合作,对方是第一次大银幕表演,现场是怎样的合作情况?
陈:我一直习惯前期做很多工作,不光是对安娜。她让我比较开心的一点,就是她的配合度真的是非常非常高,让我完全实现了对演员前期筹备所有的要求,比如说我们要首先聊很多关于角色,我会让她给另外几个配角写信,提前去适应。还要和我去宜宾体验生活,哪怕和群众演员,如果有共同的戏就需要提前彩排,是挺漫长的一个过程。我们9月份开始写剧本,12月份开机,虽然拍摄只有5天,但筹备很长。她基本都能配合我所有的要求,所以到开机现场我没有那么担心了。而且我已经很了解她了,我请她到我家来,说我过去的故事和她过去的故事。先建立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信任,然后才是导演和演员之间的沟通和信任。所以这些前期工作都做得很好的时候,你们两个人之间是有信任的,然后对人物的打磨和了解也达成共识,在现场我们已经有了想要的东西,甚至还有时间试一些不同的表达。
MW:现场重复拍摄的条数多吗?
陈:不多,因为我不是爱拍很多条的导演,我觉得可能我要的东西很清楚,我不会说这不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不对,那就再重来一条吧,我觉得这特别消耗演员的状态,我很清楚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当然我也有不清楚的时候,我会叫演员过来一起看,两个人讨论一下,哪里不对,然后再去拍。我觉得无意义的重来就真的是无意义。我不会喜欢拍很多条,但演员这一条状态OK的话,我就会给她不同的状态指导,我很喜欢给演员一个很具体的情境,很具体的想法,而不太会跟演员抽象地说,你的情绪应该是什么什么。应该给演员一个想象的空间,所以前期的准备工作非常重要。她一定是以女主人公念念的角色去体会,而不是以姚安娜的状态去代入。
MW:你能具体解释分析一下念念这个人物的状态和在故事中的性格吗?
陈:我觉得她就是一个少女,没有太思考过自我,也没有太思考过世界。就像我小时候一样,其实我并没有一开始就要去学电影,我只是喜欢电影,就自己开始拍。当时爸爸妈妈一直让我好好学习,所以我学习可努力了,一直是前三名,但第一名的时候比较多。爸爸妈妈让我干什么我会去做,就是符合社会对你的要求,当个好学生,不会思考太多。甚至在拿到纽约大学Offer前,都不会想到真的做电影这一行。所以当时真的没想为这件事要怎么样去做,没有那么清晰的想法,就是一个很茫然完全根据直觉和感受的状态。念念也是这样一个少女,洪水来了妈妈让我走就走,但还是会有些小情感,所以想去见见朋友,但是也没有准备好,想要拿个礼物送给朋友,到了那里就忘了。就是很真实的少女心态,想不了那么多考虑也不周全的感觉,但是少女的情绪是非常敏感的,你给她一点点刺激她会有很多情绪翻涌出来。所以到后来,她第一次思考,我是不是有自己的选择有自己的感受……
 MW:这个角色倾注了很多你自己少女成长阶段的细微感受?18岁出远门学电影,你的父母支持你吗?
MW:这个角色倾注了很多你自己少女成长阶段的细微感受?18岁出远门学电影,你的父母支持你吗?
陈:是的,片子中是会有我成长中的很多感受和变化吧。这个我还真跟编剧、制片大家开过一个会,讨论这个女孩是怎样的设定,我就分享了我的成长经验,非常茫然,然后在某个契机之下会有了成长的变化,你以为你长大了,然后又过了段时间发现,还是没有完全长大,只是一个阶段过去了。
父母不会说反对我,因为他们不做电影,完全不了解这个行业,帮不上我,听起来这个行业又很不稳定,很担心。但他们从来不说反对我,其实从小也没有跟我说必须要好好学习,只是说好好学习是个不错的选择。
MW:其实也就是这几年,女性电影人相对有更多空间和权利,而你看上去是个瘦弱的年轻女孩,在片场是怎样掌控70多个人的庞大拍摄队伍的,尤其是让片场的那些技术男心服口服?
陈:首先第一点,你在创作上要让人信服,你的审美、你要表达的东西要让他们认同。我觉得我能挑来非常好的团队的原因,是我的创作理念让他们相信和信任,我会和他们很细致地聊,我想表达的是什么,我的视觉方案是什么,我想怎么做,我会给他们看我以前的作品,让他们知道我之前的完成度大概是怎样。所以在创作上首先要吸引他们,大家的理念和想做的东西是一致的。
再有就是,我们上学的时候会学摄影、美术、剪辑、声音,我自己会用pro tools去做所有的声音,我是熟悉他们的工种的,我会用他们的语言和他们对话,我不会像某些导演那样,说“好,我要一个温柔点的气氛……”,特别虚无缥缈,我不会非常缥缈,包括轨道运动如何进行,到哪里该推进我都会很具体,这并不是说他们一定要按我这样做,但起码,你给出一个Plan A ,他们才会在此基础上去改进,而不是完全依赖你的团队。对一个团队来说,他们信任你就是信任你的创造力和你的执行力,还有你的判断力,你要让他们有一种归属感,换句话说,你知道自己在干吗。一个剧组里面,大家不知道导演想要干吗,就人心涣散了。
MW:现在看你像是一个非常娇弱的大小姐,但是一到片场,就换成了另外一副模样了?
陈:是的,我其实一点都不娇弱,我非常非常能出苦,也吃过很多苦。比如我在巴黎拍戏的时候,只有500欧的预算,连打车的钱都没有,我们整个剧组没花钱,用的是朋友的black Magic小相机,最后我给那个男演员100元做纪念。我所有的戏从来不找家里要钱,就是从我的生活费里出,不要家里一分钱。哦,只有一次在北京拍,但后来卖了DVD,还给他们返了利润。我从大三开始经济就已经独立了,因为当时接拍MV广告就能赚一些钱,学费还不行,但日常开销就已经足够了。毕业之后,也不光做电影,也会做一些其他的,就一直不找家里要钱了。大学四年我一直买转机的机票,第一是便宜,第二是可以去不同城市玩,一路上大箱子小箱子扛三个行李……我就是挺折腾自己的,我妈都说,你干嘛吗把自己搞那么苦。我好像就觉得花家里钱心里有点不舒服,我喜欢自己还可以给我妈点零花钱什么的。
来源: iWeekly周末画报
1,681 vi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