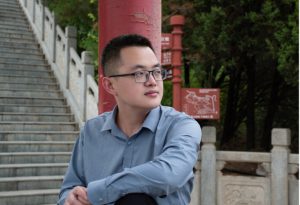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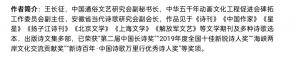
王长征诗九首
城市鸟巢
一个个孤独的鸟屋
架在冬日荒凉的枝桠上
故乡的风追着鸟羽来到城市
随之而来的还有鸟背上的云朵
以及尘满面鬓满霜讨生活的乡亲
寒夜让他们多了共同的话语
漫长的季节久久沉默
两片遮风挡雨的枝杈
顽强地扎下飘摇的根须
从此,时令节气与土地毫不相干
只有特殊节日才显现一些虚浮的繁华
家再也不是固定的寓所
成了潮水中飘荡的小舟
当繁华落尽暴露出光秃秃的本质
鸟巢犹如一盏没有隐私熄灭的灯
不得不舍弃那个温暖的小窝
去马路对面的树上重新筑巢
待春风吹来草木欣荣
它们又开始编织新的向往
我停下匆忙的脚步
想爬上树
去拥抱这些陌生的乡亲
和它们聊一聊盛开的梨花和成熟的麦子
甚至想躺进鸟屋
嗅一嗅那令人熏熏欲醉泛着潮气的树枝
好好感受片刻的宁静和温馨
城中村
灰色的楼群中间
卧着一片低矮的平房
居然有着一个土得掉渣的村名
一条铁轨扮演着“国界”的角色
一边是灯红酒绿
一边是人口挤压的村子
弄丢主人的狗像个标点
村子里逗来逗去
丧魂落魄地寻觅着残羹冷炙
2元店的小喇叭有气无力地垂下脑袋
任由人群背后扬起的灰尘沾上嘴唇
脱缰的猪羊成群结队唱着跳着
热闹的菜市场令人恍若走进梦境
苟延残喘支撑着余生
现代年轻人已不知算筹为何物
却都会精打细算过日子
漂亮的姑娘穿着几百元一双的鞋子
坐在10元自助小火锅前
黑色口腔吞吐着漂泊的故事
城中村
既不是村子也不是城市
它是地图上一块不甘心消失的胎记
一座座钢铁建筑如同巨兽逼近
各类人群动物
寄居的迷失发展方向的睡兽
终有一天它将被历史淘汰
跨过铁轨,就能步入城市
转过身,能否找到一扇故乡的门?
黄昏下的呐喊
他呐喊,天空就会下沉
白云也会随之而稀薄
呐喊停下,火焰依然蓬勃
挥一挥手
肃杀的冬季被甩到身后
抚摸着自己的胸腔
感受到汹涌翻滚的声音
惊雷般在手心震动
他苦闷,疲惫
像个无从发泄的豹子
期待情人的手
触碰滚烫的额头
他太孤独了
许久都是一个人
将各种无奈咽下
他渴望丛林的自由
却在锁链的困境中挣扎
心底呼唤亲情
竟被难以理解的涛声覆盖
黄昏张着巨大的嘴巴
要将太阳一口吞下
即将撕破的喉咙像战鼓
被木槌一声接一声地敲打!
夜晚的流浪猫
黑暗醒起
流浪猫让篮球场静了下来
城市的呼吸不再流动
凝固成墨色的花朵
猫掌踩着安静
厚厚的肉垫击打孤独
与空旷较劲
喧嚣的起义者
被夜晚逼到这个遗忘的角落
世界静的 连呼吸都是罪过
一瓣枯萎的风
想起恍若隔世的男孩
流浪猫滋长无边的寂寞
仅仅因为想起了主人
空无一人的水泥地
它只好独自背靠着
海洋般的寂静
广场
终于可以独享黑暗
旋转的世界已经停下
没有音乐,舞者失去了
火焰般的手臂
疲惫的草坪在沉睡
凌乱的脚印
被夜风吹走
迷茫的影子亦步亦趋
用沉默与我对话
黑色树枝在灯下轻轻驱赶着什么
广场从我前面走到后面
最后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
凌晨三点的北京站
从地下钻出的人群
翻开一页又一页的等待
像一群游累的蝌蚪
献出与世无争的耐心
地铁的车门犹如孕育雨点的云朵
迟迟不肯生产
生火爆意的店铺
用喇叭驱逐拥堵在门口的行人
厕所里避风的人越来越多
像一地蜷缩的烟头
遗弃在时间的缝隙
清洁工将他们一一收拢
并清理出去
难以立足的站前广场
愤懑汇聚成汹涌河流
随时都有可能决堤
天冷的像冰河世纪
人情比星光暗淡
时代的废墟上
许多人学会了顺从
大田里走出来的麦粒
在这黎明时刻焦急地盼着
开往生产线的城铁
走进王府井
有多少无情的困惑
将我们死死地缠裹
树上贫穷的鸟儿
被风肆意吹落
像一朵凋零的花
我们风中懂得
短暂的美丽不会永恒
这是京城最繁华的大街
手心里攥出汗水
吃不起最廉价的素面
举起的酒杯空空如也
我的脚印被人流淹没
找不到过往的一切
仿佛从未来过
仰首空荡荡的天空
一群天使唱着赞歌
我在激情歌声中离去
从此越发沉默
夜幕下的北京
晚间新闻开始播放
生活在不停换台
窗外是无边的夜色
室内有难熬的寂寞
写下燥热的诗句
学习孤独的生活
桌上的酒瓶
装满空洞的说教
小区楼下
一只狗无故仰面吠鸣
有人说它不通人情
我用一双筷子将它引诱
无人看见
首都繁华下的空虚宁静
月色皎洁
这恐怕是最大的讽刺
朦胧月色俯视着监控大地
本该与美酒一起引发诗人的雅兴
却张开白惨惨的嘴巴吸吮人间的暖色
它淹没灯光,化作无孔不入的河流
翻墙入户
用无情的浪花撞击
裸露的树根与黑暗的地下室
贩夫走卒们脚步更加踉跄
脚下的泥土翻卷起来
更加难以立足
也许窗子可以对抗
但玻璃的折射让月色破碎
化作更为尖利的匕首
穿黑西服的乌鸦则是天眼助威的帮凶
用一颗刚刚点燃的烟头
把不可预测的前途熏得烟雾弥漫
新西兰 澳纽网出品
编辑:小图
1,149 views



